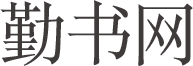第一百四十五章
不知昏迷了多久,当我醒来睁开眼的一瞬间,却是一道刺目的亮光透入,我微眯着眼睛,等视线逐渐清晰之后,才算看清四周的摆设。
我平躺在一张陈旧的木板床上,床架旁除了两个土碗后,什么都没看到。
这是一间简陋到极致的棚子,根本算不得什么房间,用十几根工地上的废旧钢管,再以铁丝随意缠绕,披上了几块厚重的油纸搭建而成。
在我的印象当中,貌似只有乞丐才会住在这种地方吧!
但让我觉得好奇的是,这间简陋的工棚却挂着很多奇怪的长纸条,黄的白的,玲琅满目,跟烧给死人的纸钱很像,每一根纸条中心都画着我看不懂的符号。
顶棚之上,还用浓重的墨汁书写着“天支地干”的字迹。
正是这些东西,让原本平平无奇的破棚子,凭空增添了几分诡谲的气氛。
整体给我的感觉很像那些土著部落祭祀用的屋子,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怪诞与神秘。
我下意识的去摸自己受伤的左手手肘,却惊喜的发现,骨折处居然已经痊愈了,而背部也一样,我从床上坐起,只感觉浑身乏力无比,提不起一点精神。
透过纸条的遮掩,我看到了外面高悬的太阳,冬日里的阳光很是温和,一束束的光线落在自己身上,感受到那暖人的温度,我几乎感动得快哭出来了。
他娘的,从小到大,老子还从来没觉着阳光原来是这么美丽,这么让人想念的东西。
对于一个刚走过鬼门关的人来说,白日里的阳光,比真金白银还要稀有,尤其是像我这种,活得了今晚,难活明晚的人,阳光里普照下的每一寸空气都值得让我留恋忘返。
这时,棚纸被人拉开,挡住了我面前仅有的光芒,露出一张冷艳无比的俏脸来。
姜丽见到我醒过来,并且已经坐到了床上,没有感到丝毫的惊讶,脸上依然保持着冷冰冰的样子。
可我见到那窈窕的身姿,居然很不争气的落下了眼泪。
“一个大男人,哭什么哭,你害不害臊?”姜丽不满的皱着眉头,嘴上虽说是在贬低我,但从她的语气里,我却听出了久违的担忧意味。
我也知道,身为一个男人在一个女人面前落泪是多不雅观的事情,连忙擦干了眼泪,平复了心境,算是破涕为笑,毕竟能活下来比什么都重要。
估计是她看我没有生命危险,便不再搭理,而是转身离去。
不大一会儿,她便扶着一个佝偻老头,颤颤巍巍的走进来。
这个老头最少也有七八十岁了,脸上的皱纹跟树皮似的,几根稀疏的白发散在头顶,如同荒原中长起的杂草,看上去很不舒服,倒是那浑身补丁的旧衣服却洗得很干净。
老头拄着一根木制拐杖,走路一瘸一拐的,似乎每挪动一步都在消耗着他仅剩的生命,我注意到,那根拐杖一头被磨得很是圆润,留下了岁月的痕迹。
直到他走近了,我才知道,这原来是个瞎子!
如果不是还能感受着他微弱的呼吸,我还以为姜丽牵进来的是一个僵尸呢。
“他是什么人?”尽管心里隐隐有些猜测,但我还是忍不住好奇问了一句。
不等姜丽发话,那瞎子老头却率先嘿嘿怪笑起来,咯咯咯的,仿佛破铜烂铁被狠狠摔在了地上,落在我耳里,简直就是一种折磨。
就是因为他这独特的怪笑,给人留下的印象实在太过深刻,任何人只要听过一次,就绝不会忘记,我逐渐回忆起,不由的惊呼道:“你就是那个救我的人?”
“哼……”瞎子冷哼了一声,摸索着床沿坐了下来,“没想到你生命力挺顽强的,我和她以为你撑不到今早,都开始为你准备后事了……”
“我去你的……”虽然这怪老头是我救命恩人,但人还没死就开始为我准备后事,这是在咒我死吗?
姜丽冷了我一眼,“你活下来也好,如果你就这么死了,我还真不好向父亲交待。”
她刚说完,老头又开始怪笑,颤抖着双手朝我脸上摸过来,这双手干枯犹如骷髅,上面布满了厚重的老茧,我心里虽极大的抵触,但终究没有选择躲开。
他的手指跟针刺一样,触摸在脸上,非常的扎人。
从额头到嘴唇,最后摸到我的脸颊,他好像要在我身上寻找什么,极为仔细且小心。
这个过程,谁都没有说话,姜丽也大改作风,紧皱着眉头,眼珠跟着他的手不断在我身上游走。
隔了很久,老头才将手掌慢慢收回去,“我看不到他的气运,就连命数都很模糊。”这句话明明是对着我说,却好似有意说给姜丽听。
“什么意思?你说明白点。”关系着自己的性命,我一下就紧张起来。
“意思就是说,谁也不知道你下一刻是死是活,更不知道你能活到什么时候。”姜丽破天荒的为我耐心解释了一句。
我心跳得极快,忙问:“难道这跟昨晚那些有关?”
瞎子老头先是点头,随后又摇头,“有一定的关系,但不是主要的,有人设局将你锁了命关,你身处的每一个地方都有可能成为一场迷局,你先跟我说说,昨晚你都看见了什么?是怎么进去的?”
我知道事关重大,开不得半点玩笑,虽然不知道这老头是不是装神弄鬼,故弄玄虚的那种人,但眼下我已经别无选择,我现在连觉都不敢睡了,长时间下去,就算不死,也定会成为一个废人。
于是,我将昨晚发生的一切,全部告诉了老头。
我极力回忆着每一个细节,尽可能将情况述说得真实一些,所以言语之间,并未有什么夸张的成分。
但姜丽听完,还是止不住的惊奇,这是我从这位美女脸上看到过最精彩的表情了。
“火葬场活过来了?怎么可能?”她连连摇头,表示不信,认为我是故意夸大事实,她说我消失的时间,不过十多分钟,在这么短的时间里,不可能会发生这么多怪事。
我就不服气了,“你不是茅山术士吗?”但话一出口,我和她几乎同时觉得不对。
首先,我度过的时间绝对不止十几分钟那么短,最少也有四五个小时,因为给我的感觉太强烈,所以我不可能记错,其次,姜丽与我感觉的时间根本不吻合。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瞎子老头一把捏住我的肩头,以一种很诡异的方式凑到我面前,突然睁开了那紧闭的双眼。
灰白无瞳的眼珠,在我的注视下,居然染上了鲜艳的血红,他低沉而缓慢的道:“你,活不久了……”
简陋的棚子内,居然在他睁开眼的一刻,飘进来一股凛冽刺骨的冷风,风声穿过棚子的缝隙,呜呼呼像有女人在外面痛哭。
我冷不丁的打了一个寒颤。
“你,活不久了……”老头那红色的眼珠,浓郁得快要滴出血来,我惊恐的想要甩开他按在肩头的手,却猛然发现,被那干裂的手掌压住,从头到脚根本使不出来半点劲儿。
这会儿,我坐在他面前,除了仅有的呼吸,僵得却跟一具尸体没什么两样。
很快,老头又重新闭上眼睛,恢复了本来面貌,我不知道他是真瞎还是假瞎,那种由里到外被彻底看穿的感觉让我极不舒坦。
我不禁联想起小时候曾听爷爷说过,世上有种人能看到常人看不到的东西,而我们能看到的,他又不一定能看清,这就是所谓的:阴阳眼。
阴阳眼的来历我不是很清楚,也从未听爷爷说过,只知道它是天生的,在常人看来,就是一种无药可救的眼疾,因此许多得了阴阳眼的人,不是瞎就是残,下场一般都好不到哪里去。
我爷爷给人看了一辈子的风水,却遵循着一个道理,不管是下料还是落仗,对天位的时候一定不能对得太准,否则会遭天谴的。
下料指的就是埋人,在风水学中有很多忌讳的词语,比如埋人不能直说埋人,要把“人”比作“料子”,不然人死之后会将怨气洒到你身上,而落仗也是一样,“仗”字通“葬”。
他一直遵守着这个底线,后来也确实应证了这一点,在他死的时候,给他来看地的那个风水先生就是一个典型的“眯眯眼”。
据说他视力极好,一本书的字儿再小都不用带眼镜的,可偏偏给人家看地时,他就看不清了。
我一直以为他是装的,现在从瞎子身上得知,那个风水先生不是装,而是真的有什么东西挡住了他的眼睛,才让他看不明白。
我见瞎子说了那一句带有恐吓性的话语后,就喃喃念叨着什么,起身颤巍巍的离去了,他声音虽然小,但还不至于小到让人听不清的地步,所以我估计刚才那一句姜丽也听见了。
她张了张嘴,似乎想要说些什么,最后却只丢下一句,“你好好休息吧。”
我一下就急了,事情都变成这副模样了,你还让我休息?我哪儿有心情啊?当即从床上起来,连上衣都来不及扣,一把抓住她的手,焦灼的问:“他说我活不久了,你也听见了吧!”
“听见了,又能怎么样?”她眼中居然透出一抹无奈,甩开了我的手。
“你不是说他能帮我吗?”她想走,但我挡在了她面前,继续追问。
姜丽挥了挥手,略带同情的说:“你的心情我理解,但你先冷静一下,这瞎子与我有些渊源,他的本事我最信得过,只要他没宣布你马上就死,一切都还有回转的余地。”
我听了她的话,平生头一次感到什么叫苦笑,“你不用安慰我了,你就明说,我还有多久?”
那老瞎子因为走得太慢,所以他刚行到棚子前就停了下来,好像是在喘气,他扶着锈迹斑驳的钢管,跺了跺手中的拐杖,“我说了,你被人设局锁了命脉,看不到命数,所以没人知道你能活多久,如果运气好,一年半载是没什么问题,如果运气差,说不定你下一秒就死了。”
我放开姜丽,立马冲到他面前,“那你能帮我吗?”
老瞎子沉默了半天,抓住我的手臂道:“你跟我来吧,但我最多只能指点你,至于你听不听,信不信那就是你的事儿了。”
我有点想骂这个老头了,姥姥的,事到如今,恶鬼见了,鬼门关也走了,平常生活中不可能发生的我都经历过了,还有什么不信的?
姜丽奉他父亲的命令,数次救我于水火之中,又想方设法的帮助我排忧解难,这次她带我来见瞎子老头,肯定是有原因的,如果我不信任这瞎子,就等同于我不信任姜丽。
我不会辜负她一片好意的。
稍微想清楚后,我点点头,咬牙道:“走吧,走吧,如果不是你和她,我都死了不知多少次了,大不了又冒一次险而已。”
瞎子老头听我如是说,不明所以的扯出让人不寒而栗的笑容来。
我望了身后的姜丽,看她一脸镇定,忐忑不安的心也稍微平静了一下。
“放心吧,不会害你的。”姜丽走过来,作势拍拍我肩膀,稍作安慰。
于是,我跟姜丽一左一右的走在瞎子老头后面,出了棚子,因为一天一夜没吃东西了,很快我就感到了饥饿,肚子咕咕直叫。
姜丽听不下去了,从兜里摸出几块饼干递给我,“这附近没什么可吃的,你先垫着。”
我心里一阵感动,不由分说的接过饼干,撕开包装袋就开吃了,我实在太饿了,几块饼干连塞牙缝都不够,三下五除二就吃得一干二净,吃完之后,却还是意犹未尽。
虽然同样乏力,但苦涩的嘴里总算有了一丝味道,我趁机低声问道:“那瞎子认识你父亲吗?”
“你问这个干嘛?”姜丽对我所问的内容,明显不太感冒,却还是答了一句,“认识,但他们两人形同陌路,根本就不熟。”
“他万一知道你父亲的下落呢?”我趁热打铁的继续说,“你找了多长时间了,当真一点消息都没有?”
我还来不及为我自己的机灵高兴,却冷不丁被对方浇了冷水,“你是装笨还是真傻?如果他知道的话,我何必来找你?跟你直说了吧,我父亲消失的时候,什么都没留下,连我那陌生的妹妹都不知道,你就别乱问了。”
我被她骂得一时语塞,想要反驳,却怎么也找不到词儿了,索性我赔礼道:“好好好,我不说了,咱不说了行吧,我跟你赔不是,对不起!”
说着,我还装模作样的给她弯了一躬,她明知我是故意的,想无论如何也骂出口了。
看她那气得通红的脸蛋儿,当真是我为数不多的一种享受啊!
一路无言,我们跟着瞎子行出了棚子,东转西拐,走了将近大半日,才来到一处荒山所在。此地方圆十里全是荒野杂草,偏生这块地盘大得出奇,远远看过去,数不清的土坡高隆,起起伏伏,漫山遍野,居然全是坟墓。
我听瞎子说,这些坟墓全是荒坟,当年位于附近的那个火葬场焚化炉发生爆炸,烧死了不少人,而这一片是当时规划出来的重工业区,不少化工厂因此遭了秧。
大火连烧三日,久灭不消,周围又无水可以调用,到了最后政府实在没有办法,为了不使灾难继续扩大,便将整片工业区隔离了起来,想尽办法将火势控制在了工业区内。
其实,这座山在很久以前原本是一片植被茂密的林山,里面别的不多,就黄鼠狼最多,城里的不少木材均是取自于此,后来木材被砍伐过度,造成严重的水土流失,生机勃勃的一座森林,从此变成了荒山。
政府为了不浪费土地,便大力将这山又重新发展起来,仅用了不到二十年,大大小小的工厂在政府扶持下建立开工了,而那些黄鼠狼一个个全都不见了踪影。
若要说当时规模最大的一个,当属那个火葬场了。
焚化炉发生爆炸的当日,正是各个工厂年关刚休完春假回来上班的日子。
那是人数最密集的时候,且荒山上生长的植被最怕的就是遇火。
常言道,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野草枯树一燃,再被山风引势一吹,可以想象,整座山上燃烧的火焰如同奔流不止的江水,向着各个方向蔓延而去,滚滚浓烟之下,无物不燃,化工厂所用的一切原料,又大多具备可燃性,甚至遇热还会发生爆炸。
瞎子指着远处说,那一天,刚好吹西北风,风大得能把人刮到天上去。
但又始终吹不灭火焰,不但吹不灭,反而还助长其势头。
以至于等到消防队赶过来的时候,已经太晚了。
那一日来上班的人,最后一个都没活下来,火势无法控制之下,是一位阴阳先生在山坳前,也就是进厂的大路上放了许许多多的“吊钱”。
说来也怪,那么大的灾难,连消防总队都灭不掉的火,却被一串串毫不起眼的“吊钱”给控制住了。
在火灾平息的第二日晚上,平空下了一场声势浩大的雷雨,将所有一切都笼罩在了其中。
然后,就起雾了,不是浓烟,就是平常的大雾,但那雾却很蹊跷,浓重得根本不能让人呼吸,但让人闻不到半点烟味儿。
那阴阳先生曾说:这里的山林本来是进贡山神所用,所谓“山神”,也就是俗称的“黄皮子”黄鼠狼大仙,这些人将黄皮子的家给毁了,惹怒了大仙,降下天灾,惩罚他们。
他说完这句话的第二年,就被人发现死在了荒山中,据目击者称,此人是被吊死的,死相很是凄惨,像生前遭遇了什么可怕的虐待,舌头伸出来一大截,眼睛瞪得老圆,而腹中空空如也,里面的内脏全被掏干净了。
让人更加不能理解的是,跟他一起吊死的还有一只脱了毛皮的黄鼠狼。
其死法跟他一模一样,腹部以下,干净得连滴血都见不到。
他说到这儿,咯咯咯的笑出声来,问:“怎么,你怕了?”
“我堂堂大男子汉,我特么会怕几只黄皮子吗?”话虽这么说,但心底总还是有点毛毛的感觉,为了不显出我的惧意,我忙转移了话题,“喂,我说,你笑得也太难听了点吧,以后还是别笑了……”我话没说完,他就凑了上来,在我耳边低声说:“实话告诉你,那个阴阳先生是我师兄,而我本来早死在那场火灾中,是我师兄一命换一命,把我换回来的。”
“我的声带,早在二十年前就被烧坏了……”
“啊!”我吓得腿脚一软,一屁股坐在了地上,惊恐的看着他,张着嘴却再也说不出话来。
姜丽不知道老瞎子跟我说了些什么,以为是我胆子太小,不过一个谣传就把我吓到,不由露出鄙视的神态,“一个大男人,你胆子怎么这么小?”
我不敢继续待在老瞎子身旁,从刚见面就总得他有点不对头,于是,我连滚带爬的起身快步走到了姜丽旁边,对他虎视眈眈。
倒真不是我胆子小,实在是这老混蛋太玄乎了,一大把年纪了,还尽跟人说些有的没的,也不知道他说的那些事情,是真是假。
不管如何,反正我是不愿跟他呆一块儿了。
考虑诸多不安全因素,我提醒姜丽,“你盯着点,我觉得那瞎子不太正常……”
姜丽听完,想都不想直接一脚就招呼过来了,她把我踢翻在地,双手叉腰,颇为不满的吼道:“喂,说什么呢你,人家眼瞎,你就说人家不正常,亏他还出手帮你化了一劫,要换做是我,早就不管你的死活了。”
“喂!”我捂着发疼的肚子,站起来跟她争辩,“老子是关心你,你要不是帮过我的话,我特么吃饱了撑的跟你唠嗑儿?”
好事不过三,我几次关心她,可到头来呢?换来的不是打就是骂,我他娘的招谁惹谁了?这些日子我受的苦,窝的火还少吗?
一群恶鬼追着老子索命还不算,一个娘们也来欺负我,我真他姥姥上辈子欠的?
人家都说好人难做,我总算认识到了,不是好人难做,是有些人压根就不服抬举。
得了吧,以后我还是甭多嘴了,人家是茅山道士,精通格斗术的大能,我算什么啊?我还是关心我自己吧。
在心里发了一阵牢骚,我也气得没去理会姜丽,跟她相处了这么长时间了,我以为我俩的关系大有改善呢,现在看来,全他妈的是我一个人在自作多情。
想想,我都二十好几的人了,直到现在连个女朋友都没有,整日整夜为了一口饭钱在奔波,到现在,差点把命给搭上了,活得真够窝囊的。
好不容易遇到个美女,他娘的对方始终油盐不进,我不禁想,难不成老子真个儿没有女人缘?
气愤之下,我抬脚就要往前走,但还来不及反应,就听姜丽着急的大喊了一句,“小心。”
老瞎子想要伸手去救我,但他年纪太大,动作迟缓,终究还是晚了一步……
听说过黄鼠狼的朋友应该都知道,黄鼠狼这玩意儿,报复心理特别强,对付比自己弱小的动物那是赶尽杀绝,尸体能给你啃个精光,就算啃不完,吃不了,这东西也绝不会给你留活路。
聊斋志异里曾提过:“凡狐鼠之流,魅魉胎光,啖肉之,性残忍……”
大概意思是说,但凡是狐鼠类的生物,与生俱来就有一种蛊惑他人的本事,且大都生性残忍无比,下手狠辣无常,尤其是成了精的,那更是孽气极重。
你不招惹它还好,一旦惹上了,那是难逃一死,以前在东北大兴安岭一带,就有不少人相信这个说法,他们那里不供土地财神爷,不供观音佛祖像,那供什么呢?
对了,专门供奉“黄大仙”!也就是黄皮子。
我接下来发生了什么事儿咱暂且不谈,在此之前,容我先给各位看官讲个关于“黄大仙”的故事,要说这个故事,就得从我爷爷祖上开始说起了……
我爷爷的祖宗叫周大叶,在清朝末年,那是当地最有钱的大地主,亩地百丈,腰缠万贯,十里八乡没有人是不认识他的。
因他名字谐音“大爷。”家里又有钱,所以不少人都叫他周大爷,以表示对他的尊敬。
要知道,当时的“地主”,就跟土皇上似的,不是达官贵人,谁敢去随便招惹?好在周大爷虽然富有,但为人却不错,附近村上的人要是有个什么事儿,来找他帮忙,他一般都不会推辞。
他平生别的不爱,就好一口酒,老子如此,作为他的儿子更是变本加厉。
周大爷一生子嗣难求,娶了五六个姨太太进门,不是难产,就是难孕,最后好不容易三少奶奶顺产了一个,却是个女娃子。
在那个封建的年代,女人的地位可不比现在,所以那个女儿自出生以来,周大爷就没正眼瞧过,更别提呵护关爱了。
直到他四十五岁那年,遇到个江湖郎中,那老郎中能掐会算,颇有点本事,但却是个天生的“缝儿眼”,看什么东西都模模糊糊的。
那时的人不懂,叫这种倒瞎不瞎的为“缝儿”,现在有了科学的名词,实际上就是“青光眼”,老人最容易得的一种眼疾。
老郎中告诉周大爷,你命中冲煞,五命缺一,至于缺的是什么你心里清楚。
周大爷本来还不信,但一听这话就愣住了,是啊,自己一生荣华富贵,权位相加,就是县大老爷看见了自己都得点头哈腰,礼让三分。
要说缺什么,不就缺个宝贝儿子嘛。
于是,他知道自己遇上贵人了,连忙恭恭敬敬的将老郎中给请了回去。
那几日,家里是杀鸡宰羊,大摆宴席,周大爷被别人伺候了一辈子,不曾想有朝一日也会伺候别人。
外人见了就要说了,请回来的那个不会是个江湖骗子吧,最近这几年刚好碰上闹旱灾,庄稼本来就难种,偏偏又犯了黄皮子,那些狗日的东西将农民辛辛苦苦种出来的庄稼给糟践的一干二净,以至于颗粒无收。
不少人都背井离乡,逃冬荒去了。
因为东北的冬天很冷,可以将一个人活活冻死,农民没了庄稼,政府腐败无能,无法开仓赈粮,所以只有往南方逃。
很多外人都说那个老郎中实际上就是“冬荒犯子!”来周大爷家骗吃骗喝的。
可周大爷求子心切,哪里管的了那么多,况且百十亩地难道还养不活一个老头吗?
老郎中在他家住了差不多半个多月,半月下来,将他府上内外给算是看明白了。
一天晚上,他将周大爷喊到自己屋里来,对他低声说道:“我看了你家宅基,差根儿,也就是脉相不足,所以不管你娶多少姨太太进门都是没有用的。”
周大爷一听急了,“大师,那你赶紧想想办法啊,俺这辈子啥都不缺,就缺个命根儿啊!”
老郎中一摆手,说:“不急,待我今晚准备一下,你明天这个时候来找我。”说完,不分青红皂白就把他给赶出去了。
而自己却在屋子里,点上油灯,捣鼓了一个通宵,直到第二日鸡鸣,才见他熄灯睡觉。
事关自己一脉传承,周大爷能不着急吗,第二日天还没黑透,他就又找上门儿来了。
这时,老郎中走出屋子,对他说:“你赶紧去杀一只鸡,取三碗鸡血,在叫人弄一碗黄米来,带上三炷香,咱就为你化煞去。”
周大爷心中一喜,自然不敢怠慢,忙喊了下人,将老郎中所说的吩咐了下去。
不一会儿,东西备齐了,老郎中端起其中一碗鸡血,就朝他家大门走去。
走到大门前,他眯起眼睛看了一眼门梁,又望了一下地基,然后伸出手指,开始乱搓。
周大爷的几个姨太太觉得稀奇,就都出来瞧热闹,街上过路的人也很少见过,围在门前,七嘴八舌,议论个不停。
只有周大爷一个人心里那个焦急啊,盯着老郎中一眨不眨,生怕出了什么乱子。
也不知道老郎中转了多久,从正门转到东屋,再从东屋堂窜到西屋,在不懂的人看来,就像跳大神一样,神神叨叨的。
有句话说得好,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
这老郎中哪里是在跳大神,在阴阳学中,这一步骤叫“寻三缺”,就是定方位的意思,三缺又指:“福寿禄。”
周大爷家钱权正旺,对应了福禄两不缺,缺的正是寿!
各位看官,这个寿可不是人们常说:“福如东海寿比南山”里的那个寿啊。
而是血脉传承的寿,阴阳里面对每一个字都有着很多解释,三缺就是其中一种。
只有知道差在哪儿,才能补哪儿,老郎中也算是“吃阴饭”的一类人,跟他相同的还有一种叫“账房士”,也就是俗称的“通算先生。”
大抵跟后来的什么阴阳先生,茅山道士一样,只不过当时分不了那么细,也算是对这类人的一种统称吧!
总之,老郎中找来找去,最后定在了他家厨房门口,他对周大爷说:“最近闹饥荒,不光人没吃的了,就连那山上的黄皮子都没得吃,你既然不缺粮食不缺钱,那就散点出去,当做件好事儿积德,怎么样啊?”
周大爷一心挂念着宝贝儿子,哪里有半个不字,当即连连点头,“中咧,咋不中啦,大师咋说,俺就咋办。”
于是,接下来发生的事儿是任何人都没想到的……
老郎中见周大爷如此慷慨,也没往多处想,只是在行事之前,再三嘱咐他,“你命中犯缺,我帮你把这一缺给补上,但你要遵守三个条件。”
“什么条件,你就说吧,只要不是要了我老周的命……”他拍了拍胸脯,想到自己万贯家产,倒也真没什么好怕的。
老郎中疑神疑鬼的将他拉到人后,伸出一根手指说:“其实也不难,这第一就是从此以后你再也不能沾酒,第二每年这个时候要记得给黄大仙进贡,第三就是不得杀害任何一只黄皮子,你若做到这三点,黄大仙会保你家族三世太平,如果做不到,你就等着遭天谴吧。”
这时,周大爷就不解了,后面两个虽然不明所以,但要照做也不难,可就是第一个条件,让他有些踌躇了,在没儿子之前,酒就是他的命根子啊。
突然就要他一个大老爷们戒酒,到底有些强人所难。
他瞥了老郎中那严肃的脸,心道:老子喝不喝酒,还轮不到你来管,大不了这段时间不喝就是。
想罢,就虚情假意的应了下来,老郎中欣慰的点头,不再废话,叫人取了另外两碗鸡血,放在灶台前,三柱清香一点,往黄米上一插,然后虔诚的跪在地上,又是磕头,又是鞠躬,行为举止,小心无比。
口里还不断在念叨着什么,只不过声音太小,任何人都没听见。
做完这些,老郎中从屋内退出来,神色忽然疲惫了不少,对他说:“我替你求了根儿,今晚全部回去睡觉,谁都不许在外面瞎转悠,不管半夜听到什么响动,也不许出来,等到明早儿就知道答案了。”
一听这话,周大爷带着几个姨太太是千恩万谢,然后他就下令,府内上下的仆人今晚全都不用忙活了,厨房里的伙夫一样,全都照大师的话做,谁都不许出来,不然一百个板子伺候。
仆人伙夫们哪里敢不从,又见这事儿邪门,天还没黑透,就闭了府门,宅邸内再无人走动。
入了夜,周大爷躺在床上,总感觉心里毛躁躁的,静不下来,心里惦记着白天老郎中说的,翻来覆去始终睡不着。
过了不久,他果然听到屋子外面传来蟋蟋洬洬的响动,像是有小偷在翻东西一样。
说来也怪,在他听到这阵响动没多久,他就迷迷糊糊睡着了。
等到第二天早上起来,跑去一看,那盛满鸡血的三个碗,干净如初,就连黄米也是一粒没剩。
老郎中笑着对他说,成了!
周大爷要留他下来,表达自己的谢意,但老郎中说什么也不在逗留,当晚就背起自己行囊,于初月走了。
临走之前,再次嘱咐了他,还是同样的话。
此事过后的第二年,年关刚开最小的一个姨太太就给他生了一个大胖小子。
胖小子名叫周喜胜,取名字的先生说,这小子面相极旺,五行啥都不缺,他命比你周大叶还要好哩!
从此以后,周大爷乐得合不拢嘴,见谁都是笑哈哈的,但好景不长,在他儿子二十岁那年,闹了史上最大的一次旱灾,土地干涸,裂开的口子有小手臂那么粗。
另外顺带一提,自周喜胜出生后的二十年来,周大爷其余都照做,但就是一点,嗜酒如命的毛病始终改不掉,最后他儿子也照着学,酒量越来越大。
起初周大爷见了,好歹也训斥了两句,但看周喜胜一天天长大,也没什么不对,索性就不管了。
爷俩儿经常喝得酩酊大醉,而且他一喝醉了就爱忘事儿,酒精熏陶之后,关于几十年前老郎中的那些嘱咐也全当成屁了。
恰恰是这一年,旱灾从来没有这么严重过,方圆十多里的几条大河全都见底了,整整一年多愣是没下一滴雨。
没水没粮食,不少酒坊酒窖相继倒闭,这下就算他想喝酒也没处买去,只能是靠着每天官府运水过来,用钱买下十几桶,藏起来作酿酒用。
最后,官府也没来了,水没了,十里八荒名不聊生,大伙都知道,如今有水的只有他周府了,但那是他藏起来酿酒用的,能随便拿出来吗?
这一天傍晚,照例又来了几个讨水讨饭的,最近来的人可多了,周大爷碰巧不在家,周喜胜自然就是当家了,他一个人喝醉了,走路都打颤,看人也看不清,走到门前只看了一眼,就要将那些人轰走。
其中有个人就说了:“当年我们把你送来,到头来你就是这么对我们的?”
说这话的是个老太太,面白得跟纸似的,脸上几乎见不到半点血色,看上去有点渗人。
周喜胜哪里听那么多,“滚滚滚,老子是周家大少爷,你们几个什么东西,也有资格来管我?”
这话刚一落,讨水的那几个人也不再继续跟他说什么了,而是背过身去,凭空消失了。
活了二十年的周喜胜哪里见过这些东西,他以为是自己喝多了,眼花根本就没在意。
后来,周大爷赶回到家,他从儿子口中听说了这事儿,心里才猛地想起那老郎中说的话,不由一拍大腿,慌道:“完了。”
果不其然,从那以后,周大爷每晚都听到有人在厅堂嚎啕大哭。
而自己私藏的那些酒啊,水啊粮食什么的,平白无故越来越少,最后全见了缸底。
一晚,周大爷照例喝了点小酒,半夜起来方便,刚出屋子就又听到那哭丧的声音,好像还不止一个人,呜呼咿呀跟唱戏似的。
这一听,他不自觉的出了一身冷汗,酒精也随着汗液被排了出去,夜风一吹,止不住的发抖。
他给自己壮了壮胆子,心想:这特么什么时候了,到底是什么人每晚都来我家哭丧啊?
正当他顺着声音往正堂走去,突然有人从背后拍了一下,冷不丁将周大爷给吓了一大跳。
拍他的正是周喜胜白天见到的那个老妇,此刻这个老妇披麻戴孝,正跪在他面前,面色苍白如纸,腮上像是用胭脂点了红,嘴唇也是红如鲜血。
就跟村头匠人扎得纸人一样,样子渗人到了极点。
他拉着周大爷的衣袖,哭丧道:“你个没良心的东西,当初费尽周折帮你把儿子弄来了,到头来你就是这么对我们。”
老妇刚一说完,那厅堂内跪着的十几个人,全都披麻戴孝,头戴白纸尖帽,对着厅堂上的一个灵牌,越哭越厉害。
周大爷正眼一瞧,顿时吓得魂不附体,那灵牌上写的名字正是“周大叶!”
此后没过两年,周大叶就得怪病死了,临终前都还在念叨着自己对不起谁谁谁,不该怎么怎么样,即便下了料子,落了仗,最后也被黄皮子来刨了老坟,将尸首啃得到处都是,那下场怎一惨字了得。
都说富不过三代,周家财产便从周喜胜这一代开始逐渐没落。
倒也证实了当年老郎中对他的那些嘱咐,怪也只能怪周大叶自己从一开始就没遵守,因果轮回,报应落到了自己的下一代,不但将万贯家产付诸东水,就连后代都接连遭了秧。
从那以后,这个故事就在东北流传开来了,老人们常说,做人要厚道,不能像周家那样,应诺之事,从不兑现,落了个悲催下场。
所幸的是,恩仇不过三代人,更有种说法叫,四代血缘为一家,意思是说,不管前人们做了什么错事,遭受什么样的报应,都绝不会殃及第四代人,大部分的家族史都是从第四代便另起一家了。
这事儿到我爷爷那辈儿,也算了结干净。
可追根究底,到底是有些渊源,少年时期的我,比较调皮,最喜欢的一件事莫过于折磨小动物了,尤其是喜欢折磨老鼠。
那浑身黑不溜秋,行为鬼鬼祟祟的小东西,实在是令我讨厌之极,每次让我逮到它,不是被我活活踩成肉酱,就是拿绳子系上,然后钓进开水里,看它在锅里不断挣扎的样子,放声大笑,行为手段可谓是无所不用其极,只要是能想到的狠招酷刑,基本都被我用了一次。
爷爷曾说,老鼠这东西实际是黄皮子的亲戚,只不过两者血脉不同罢了,就好像黄种人与白种人一样。
那时的我压根就不信这些,还常常反驳他说,生物课上讲黄皮子跟老鼠虽然同样是啮齿类鼠科,但黄鼠狼还经常捕杀老鼠呢,哪个亲戚会捕杀自己的同类?
爷爷摸着我的头,叹气说:“孩子,你还小,还有很多不懂,以后你大了,自然就明白了。”
以前我对老鼠做的那些事儿,现在也分毫不差的报应在了我身上。
这个时候,我才明白过来,不管过了多少年,只要当年周家的血脉没断,那么这个诅咒就会一直持续下去。
所谓,不是不报,时候未到!
我在落下去的一瞬间,恍惚中甚至看到了一张老妇人的脸,在底下冲着我笑,而下面好端端的泥土,在我眼里,突然就变成了流动的鼠群,黑压压一大片,蠕动不断,让我头皮发麻。
由于这块地盘被废置很久,杂草疯长,不少草芥子早已没过了人腰,其中隐藏着看不到的芒草,惊恐之下,我一把抓住斜坡上的草根儿。
哪里想得到,那芒草的倒钩锋利如镰刀,手上还没使劲儿就被划拉开一条狭长的血口子,此刻,我半个身子都已经没入了进去,草莽挡住了老瞎子和姜丽的视线,他们自然看不到我下面的情况。
事实上,就算没有草莽遮掩,他们也看不到我所能见到的景象。
慌乱之中,我几乎能感到脚踝处传来阵阵的瘙痒感,像是有一万只蜈蚣不断向上爬来,我拼尽全身气力,指甲死死抠进泥土里,同时仿佛溺水般,脚下疯狂的乱蹬乱踩,嘴里大喊:“救命,救命啊……”
要说在这荒山中,一无凶兽,二无险地的,遇险的几率应该很小很小才对,而且我掉落下去的地方并不高,最多只有两米,也不至于将我活活摔死。
若换作别人,铁定以为我是在跟他开玩笑,但姜丽凭借着自己的直觉,立即判断出我确实有危险,不容她多想,直接一把夺过老瞎子手里的拐杖,蹲下身子,焦急的对我大喊:“快抓住它。”
老瞎子却比我想象的要从容冷静许多,他从衣服里拿出一瓶白酒,拧开酒瓶子,一股脑全部往我身上倒。
酒水哗啦啦往上泄来,将我从头到脚都给淋湿了,我一闻,这酒酸中带有苦味儿,刺鼻之极,我知道这是雄黄酒,与黑狗血一样具有驱邪避障的功效。
而且,也不知道瞎子那拐杖到底什么木头制成的,我一把抓上去,居然感到了一丝阴冷的气息从头顶游走到全身,配合着冰冷刺鼻的雄黄酒,让我禁不住连打冷战。
被酒水浸透的我,莫名其妙的就涌上来一股力气,而底下死死抓住我的那个老妇,面现惊恐的慌忙松了手,似乎很是忌惮这雄黄酒。
当我被姜丽一把拉上去的时候,我还隐约听见了一句诡异的话,“别看你找了人,我也不怕你,你逃得过今日,逃不过明日……”
我扶在土坡上大口喘气,随后像个疯子一样朝着空无一人的底下大喊:“操你妈的,老子又没招你惹你,该死的黄皮子,别让老子逮着,逮着老子非剥了你的皮。”
如果这是在前几天,估计我早就被吓瘫了,哪里还骂得出口,只不过见多了,胆子大了,但我一想到刚才那群蠕动的鼠群,就犯恶心,本来一天没吃东西了,结果一吐出来,全是黄疸水,眼泪鼻涕流了一大把,过了好大半天才算缓过来。
老瞎子却不慌不忙的对我笑着说,“看吧,叫你不信邪,刚才我说什么来着?”
这会儿,我浑身不得劲儿,也难得跟他废话,自顾自的躺在地上,摆成一个大字形,闭着眼休息。
姜丽从始至终都没搞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她看看瞎子,又看看我,问:“你该不会又着道儿了吧?”
我呵呵笑了两声,实在没有力气再去搭理她,就那短短的一分多钟,十条命当先去了九条。
老瞎子却说,“黄皮子这东西,一旦犯上了,除非你将它赶尽杀绝,否则它们不会放过你的。”
我告诉他,刚才底下露出一张老妇的脸来,苍白无血,看上去比你还老,那该不会也是黄皮子变的吧。
“狐狸尚可成精,黄鼠狼为何不可。”老瞎子伸出手掐了几下,说:“你祖上说不定是欠下了什么渊源没还完,恰到了你这一代,出了个阴阳者,我估摸着那老太太是寻债来了,你眼下身中迷局,无法抽身,恐怕也跟此有关,要想破局,首先还得将那些恩怨给算清楚,不然越到最后,麻烦越多。”
听完,我盯着昏暗的天穹,叹道:“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