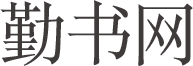第一百九十四章
“要是那是封情书,我就算了,好歹我恭喜你一下,要那玩意儿就是张白纸,别人逗你玩儿的话——你可千万别再拉我干任何事。”胖子一脸的晦气,我入神地看着胖子,思考着要不要把爷爷的事儿和胖子也说说。虽然说胖子这货外面花里胡哨,没个准头,但行动能力比我强,起码够义气。
应该是可以的。
于是我把胖子拉出去,胡吃海喝了一顿,回到寝室,两人躺在床上,一边消食,我一边打开话匣子。
“胖子,我和你说个事儿,这事儿,疙瘩在我心里好多天了,也不知道该不该说,老实说,我觉着这事儿也挺傻逼的。”
我一嘴的韭菜饺子味对着天花板说着。
“所以你拉着我一起傻逼是吧?好——承蒙你看得起,胖子我就指导你傻逼一回,说吧。听着呢。”
我想不出怎么起头,捉摸来捉摸去,想着有什么说什么就是了,于是我把脑子里能记住的所有的爷爷跟我讲过的那个故事和胖子说了一遍,然后再那本笔记的事情也和胖子说了但是我爷爷失踪的事儿,我没说。
说完,我就想听胖子的意见,只是他半天没声,这孙子不会听着听着睡着了吧?
胖子突兀地说道:“这就没啦?”
我嗯了声。
不料胖子就在床上就笑了起来,边笑边说:“诶哟喂,缺儿,诶,您等等,我这笑还下去,还得笑一阵子。”
胖子自个儿在那胡乱笑了一通,我也不知道他笑些什么,但是他一笑,我就在旁边很傻逼。我叫胖子别笑了。
“你还真相信你爷爷说的那些啊?”
老实说我是不相信的,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我没那么有底气。觉得爷爷应该讲的不是故事,而且回忆起来,爷爷那个时候也挺严肃的,不像是讲故事的调调。
胖子见我不做声,便说道:“瞧你还真挺真诚相信你爷爷说的。我们这就来算一笔账。你说的那会儿是上世纪30年代,你爷爷当兵,瞧着里面年纪不算小应该是18岁往上走对不?”
“那又怎么样?”
“你加加时间就知道问题在哪了。”
爷爷那个时候18岁的话,那么按照胖子的话,现在都21世纪了,中间隔着将近80年,那么加上爷爷的18岁的底子,爷爷现在岂不快要一百岁了?
我脸色顿时白了,这肯定不可能,我爷爷虽然说也一把年纪了,但是我奶奶都只有70多岁,怎么会爷爷快有100岁。虽然我不知道爷爷到底有多大,但是肯定不会有那么老。
“你家老爷子有这么个岁数么?亏你还在辩论赛训练过逻辑,竟然这么简单的一个逻辑缺陷都没看出来。”
也算是我当局者迷,只注重过程,没想到过要在时间上考虑,这一想起来,如果爷爷没有那么老,那么发生在30年代的事,他怎么知道,而且知道地这么清楚,就好像亲身经历过似的。
“你可别纳闷啊,我告诉你,老北京那会儿茶馆说书的,他能说着说着眼泪都流下来。什么七侠五义啊,讲的惊心动魄身临其境,甚至都能把武松穿什么花色的裤子都给你说的一清二楚。老爷子顶多是个说书的高手,别较真儿!”
难道爷爷这真是哄小时候的我,随口讲过的故事?可是他的笔记上写的那些故事的后续又怎么说?难道一个人讲故事讲上瘾了,还把故事的后面都写下来?关键他写就写,怎么写成这种类似日记的形式,这说不通!
我把我的疑惑和胖子说了,另外告诉他我早上那会送过去化验的,不是别的,正是我爷爷的笔记上撕下来的那些字迹已经消失的纸张。
“我说呢!吃饱了撑的,哪个女生会寄无字情书。你小子下次有话直说,哪里来那么多花花肠子?知不知道天妒英才,聪明过头,死得早?那你现在怎么办?等化验结果?”
我对着胖子摇了摇头“不是,现在要做的是找一个人。”
“谁啊?”
“一个妞。”
早上一起来,我就想着要去辅导员办公室那儿要来江怜亘的宿舍号,只是去了以后,发现江怜亘压根不住宿舍。有学生反映给辅导员江怜亘在外面住,说是她的详细地址有,但是没有核实。
辅导员和蔼地说:“你来的刚好,老师这有事要你帮下忙,这江怜亘住在外面,一个女生,老师也不放心。现在这一阵子外面抢劫的作乱的事又多。诶这要是班上有一个学生出了事,我的心就揪着痛。老师对你比较放心,你去江怜亘那儿看看,她是不是真的住在那,详细问问她为什么住在外面,寝室多好啊,有个照应,也不孤单,还安全……”
我去的时候一腔子热情,硬是被辅导员长篇大论的爱民如子的情怀给消磨地丝毫不剩。
被嘱咐一番,不过这样也好,扛着差事去,也有个理由,免得师出无名。
一天都有课,等我空闲下来,已经是晚上了。江怜亘这个怪胎,连课都不来上,没办法我只有按着地址去找她。
地址倒挺好找,就在我们医学部对面靠着义湖的那地儿,有一栋公寓,公寓四周林林散散有些养路工人的小房子。江怜亘就在那林林散散的小房子中,听说是找一个大爷租的,顺便帮他照料一大片荷塘里的鱼。
我按着特征找,还真被我找到一户。这房子东面是义湖,北面就是一大片荷塘,南面栽着松衫林木,一进去好像就迷失在了自然中,几乎隔绝城市的纷扰。
房子红瓦粉墙斜合顶,倒是不大,七八十个平方,一个人住绰绰有余。
我肚子里打了腹稿,便要往那房子走去,只是转过了树木的遮掩,发现荷塘边上蹲着一个人。瞧那身形正是江怜亘。
这丫头晚上蹲在荷塘边干嘛?顾影自怜?我蹑手蹑脚走过去,站在她身后看着她在干嘛。
她的身旁放着一个大盒子,里面装满了鱼饵,她抓了一把,掂量掂量放回去少许,然后像是在汤里细致撒盐似的,将鱼饵投进荷塘里。水面下很多金鳞在游弋抢食鱼饵。晚风吹皱了湖面,也吹散了她的刘海。她笑容美好地看着湖面,状似极度开心。
我愣在一边不知道怎么开口,有些不忍打扰这样安宁的美好。于是悄悄地走到她的另一侧,然后抓着鱼饵要往荷塘里投下。
声音惊动了她,突然身边多了个人,把她吓了一跳,不过让我吓一跳的是她竟然用力推了我一把,蹲着本来就重心不稳,这一推,我犹豫半天后,竟然就控制不好平衡一下栽了下去,把荷塘炸出一个大坑!
我栽下去的那一瞬间心里就大骂,这女人疯了吧,应激反应这么强烈,这谁还敢打她主意,辅导员还用得着担心她?辅导员肯定脑子有病。
呛了几口荷塘的水,我才被她捞了起来,还好我会几手狗爬,要不然就喂鱼了。
她把我请到屋子里,然后拿了干毛巾给我让我擦擦,一边去煮热水一边问我,怎么到这里来了。
“我——阿嚏,辅导员让我来的,说——阿嚏,看看你。”
这11月份,水特别凉,一起来人好像跟全身贴了冰块似的。我四下打量她的房间,由于是林木工人的房子,主要是给工人们养护树木的,所以房子也没在设计上下什么功夫,整个房子卧室客厅,厨房都连在一起,只有厕所是另备一间。
房子里面很清爽,不像一般人的房子怎么看都有些凌乱,墙的四壁都挂着很多素描的图像,画的很逼真,但是翻来覆去就是那么几个人。
多打量就不太好,我又把目光放在她身上。
我瑟瑟发抖说:“辅导员说——你在外面住,小偷啊,抢劫的啊,强奸的啊群雄并起。这不都快过年了,不干好事的想要大捞一笔,混个年费出来。事情乱的很,叫我看看你这情况怎么样。”
她远远地站在一边看着我“我没什么问题,倒是生活委员恐怕你得多保重身体。”
去你娘的,不是你手残,我能犯得着在荷塘里泡澡么?
是不是应该回去换个衣服再来?冷的我骨头都酥了。这样下去,铁人打的都扛不住。可是现在都已经八点了,换个衣服再来,估计就九点了,这九点再交流一下的话,岂不是回去学校就关门了?那我晚上住哪?还是忍受一下痛苦,该问的问完,然后跑路。
我正要说话,她那火红色的眸子就盯着我:“该不会只有问候我这些东西吧?生活委员?”她俏皮地看了一眼,但是眼中很是骄傲。
“得,我还真不是来问候你的,老实说我其实还算很敬业的,要是我没急事,那我还真就跟你客套两句。说吧,你面纱那首诗是怎么回事?”
她的眸子中有些东西在变,我一说出来的目的后,整个氛围就在奇妙的改变。江怜亘也有这首诗,而且是在教授没有告诉她的情况,自己就已经对这首诗有了疑惑,看来她一定知道些什么,知道一些我和教授都不知道的事情。
“我倒的确是说过——你赢了我,便可以问我,不过我——现在不是很想回答。而我现在想做的事——就是从你口中得到关于这首诗的事情。”她慢慢地退后,神情渐渐变得苍白而且冷酷,原先的那种温和都在慢慢地消褪。
一下子气氛低到零点,好像不管什么人遇见这个问题,都神经莫名紧张,这首诗后面到底有什么玄妙,爷爷为什么要留下这首诗给我?
她越来越退,一下子就退到了她那卧室的床沿。
很多往事涌上我的心头,爷爷对我小时候诸多的疼爱,还有爷爷失踪的事情都在我脑袋里盘旋。
这两天我的精神状态很是不稳定,处于一种极度焦躁中,频繁看到和爷爷有关的线索,但是我总也得不到答案,这使得我的脾气变得糟糕。对教授我还能克制,但是对江怜亘可就二话了。
我一把冲上前去,就要抓住江怜亘,根本不打算好言好语,什么哄骗,什么祈求的腔调和她说了。不说直接就狠揍一顿,虽然我一向是最尊重女性,可是我已经在这件事情上面没有耐性了。
谁知道这丫头突然在床头枕头下面抽出一把枪来,看起来有点像格洛克,美国的民用常备枪械,杀伤力不算太狠,但是这个距离干掉我,一点悬念没有。
这丫头什么情况?竟然私人藏枪?这就算了,老子又没污你清白,你犯得着话刚开匣子就拿枪指着我么?
“请退后!”她的脸色由苍白化成诡异的冷静。
我一时间脑子就炸了,这是我第二次遇到不可抗力,小学有一次我们这余震,教学楼震得直晃,那个时候第一次有了我快要死了的念头。不过最后虚惊一场。
这一次可是真的一把枪顶在我头上,话不对头,立马就脑子开花。这他妈太狗血了吧?不是都是男的拿枪顶在女的头上,然后为所欲为么?怎么事情发生到我身上,就颠倒了?
我刹住前冲的步子,心头的烦躁立马凉了下来。“冷静,冷静,江怜亘,你要冷静。你这是——这是干什么你知道么?”
我颤声地问着她。
“我当然知道,所以你趁着我还能保持清醒的时候,赶紧把你知道的所有关于那首诗的一切,给我说出来!现在!”她对我轻轻地吼叫。
我他妈就是不知道才来找你!
可是这句话打死都不能说,说不定她会怀疑我知道但是不想说,这无疑是激怒她。现在太诡异了,我实在想不到在同学之间,就在校园外几百米的地方竟然会发生这种电视剧上才有的情景。
听说在零点零几秒的时间内可以躲过子弹,估计我是不行的,但是不知道胡一菲的弹一闪可不可以。
“那首诗——你可以放下枪来,咱们好好地说啊,犯不着这样是不是?”
我慢慢地后退,然后抓着门框,还差一步,就能出这屋子,一出这屋子,我就可以有机会逃出生天。谁都想不到,来查找线索,竟然把自己弄到死地来了。
她把枪上了膛,沉声道:“你再退一步,我就开枪,我不会让你这样逃出去的,你可以考验我的冷静。”她火红色的眸子狂躁地看着我,我不由自主慌张起来。
她的眸子里的感情太强烈了,好像把我当成死敌一样,我有八成把握,只要我再动,她就会开枪。
“有话,好好说啊。”事到如今只有期待变故的发生。
她说道:“我不需要废话,把你知道的关于那诗的事情,全部告诉我,下一句话,如果还是废话——”
事情到这个地步,实在已经极大出乎我的意料,她对这首诗的敏感已经远远超过了我。这首诗的背后到底隐藏着什么?爷爷为什么要留下这样的讯息给我。我心下念头急闪。
“我学过心理学,你要是在0.7秒时间里没有回答我的问题,我就会认为你在拒绝回答问题,或者在思考怎么骗我,这个时候我就会开枪!”她好像在念说明书似的对我说着。
这女的疯了吧?
“是谁告诉你的这首诗,你自己找到的还是别人告诉你的?”
她的声音里有不容置疑的权威,很明显她真的会开枪。
“别人!”我立马回答道。
“是谁?”
没有办法,反正我不知道她为什么会这么激烈地对我,但是肯定是有原因的,我如今可以把知道的告诉她,最后的时候或许可以从她那里也得到相关的情报。反正我对整个事情都没有参与,如果有什么恩怨仇恨在里面,也牵涉不到我。我告诉她一些信息,至少可以让她冷静下来。
“我爷爷。”
“你爷爷是谁?”
“这我怎么回答,难道说他的名字,你肯定不认识好不好?难道把照片给你看看?”
我一时间犯了贱,嘴贫了一下,但是她丝毫不受影响,硬逼我告诉了她爷爷的名字。不过看来她的确不认识爷爷。
“你爷爷在哪?”
“失踪了。”
“失踪了?”她一下子皱起了眉头。
“好像一群记者绑架了他,至今不知道他的下落,我找你的原因不为别的,我爷爷给我留下了笔记,笔记上面有这首诗,然后我爷爷就失踪了,所以我看见你面纱上的诗,我以为你会有爷爷的线索,所以这样问你。你要冷静。”
我对着她安抚,她刻骨铭心地看着我好像要把我看透,是不是在说谎。她没看出端倪。
她对我的神色渐渐放松下来,拿着枪的手不再绷直。
这个时候外面有狗在不停地吠,我看着她,她也没让我动。似乎我说的信息对她并没有威胁,她对我现在放松了警惕,但是并不是完全放过我,从她仍然没放下扳机就可以看出来。
这女人到底从哪冒出来的,难道不知道中华人民共和国不能私自拥有枪械么?你千万别让我逮到你,要不然有你好看。
狗吠了半天,见没人理它们,竟然有好几只狗,跑了进来,它们对我颇有些警惕,但是一看见江怜亘,便乐开了怀,挤着往江怜亘身上蹭。看的出都是一些花色很杂的流浪狗,身上虽不脏,但一个个饥肠辘辘。
不知道它们怎么对江怜亘如此亲热,各个去舔她的脚。这拿枪的gunman竟然还受到如此欢迎,我一个无辜的人,狗都不理我。
因为房子铺的是木地板,江怜亘没有穿鞋,光着脚丫,被狗舔,她有些耐不住痒。传说女人脚上有敏感区,难道这是真的?
我不知道从哪里来的勇气,趁着她神色不属的那一刻,一把冲了过去,抱住她的手腕,将她的枪砸飞。同时大力之下,将她按倒在地。由于她在床边,这一扑倒,便让她脑壳撞在了床边,她神色剧痛,好看的脸都皱了起来。
要说我绝对不是一个狠心的混蛋,不会怜香惜玉,可是江怜亘这个女人实在太另类,一进来就拿枪指着我,不能常理视之。最好在面对她时,让她丧失所有攻击能力,才是最安全的办法。
我跪在她身上,两只脚按住她的胳膊,同时手掐着她脖子。本来照我的意思是先打她个半死,但是好歹人家是一个闺女,还是没忍得下手。
但是被人用枪指着,一分钟受的罪不是可以描述的,我现在没发起疯来,用枪指着她已经很是不错了。
她被我掐的直翻白眼,用劲之大,在她脖子上勒出淤青。老实说我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那么做,人在紧张状态下做的事情都很出乎意料,人本来是从动物进化来的,一旦生命受到威胁,便会激发人类的本能,那就是保命——或者逃跑,或者将对方弄死。
眼看她就要晕过去,我放开了手。
脑子被狠狠撞了一下,外加脖子被狠狠掐着,估计她这一趟也够受。谁叫她没事拿枪指着大老爷们儿的头。男人的头女人的腰,狮子的屁股,这些都动不得,幼儿园老师没教过你?
“我和你有什么深仇大恨?你要拿枪指着我?”我恶狠狠地对着她说,情况一下逆转,我得狠狠把场子找回来,我才不管你当时和我辩论过,你还是我的同学。事情到这个地步,你唯一的出路就是把一切都告诉我。
“你掐死我啊?咳咳。你掐啊!你不是要报复么?”她好像枯萎的花朵,对着我神色倔强,但是绝美的颜容在她身上重新焕发光滑,她刚才那些冷酷都消失不见,一下子又成了纯真可人的女孩,让我这么下手有些罪过。
我琢磨是不是应该放开手,和她好好谈谈,毕竟也没什么事情发生,被枪指着,吓我一跳,这事我也认了。
我神色松动,无意间看着她那火红色的眸子,那种要放开她的想法就放弃掉了。既然都做到了这个地步,那就做到底,直接这么问她,免得待会起来故事又回到原点,像教授似的跟我绕圈子。
“现在对不起了,轮到我来问你了!我不会要求你在0.7秒内回答我的问题,但我一定会把你肠子掏空,把你所有知道的都挖出来!”我凶恶地说着。同时握紧了拳头。
“你的诗是怎么来的?别人给的,自己找到的?”我用她问我的方式,问她,也算报了仇了。
她直勾勾地看着我,但是她的脸色很不好,不知道是不是想起了什么往事。她的身上那种馨香让我很难暴躁起来,但是现在已经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了。
“你不说?那你可别怪我,这在法律上算是自卫,你用枪袭击我在先的。”我自己给自己找台阶下,好让自己打人有理,可是她像个不怕狠的猫似的,拿眼睛凶我,压根不退缩。好像压根不相信我会揍她,又好像说就算你揍我,我也不会说的。
我学不来她那种冷酷的神色,拳头举到一半,还是放了下来。要下手真的很难,我的眼睛就出卖了我。而刚才她的那样子完全不像作假,看来她是真的时刻准备开枪。
一想到这我就来气,你对我一点感情都不讲,我跟你五讲四美以德服人个屁,直接揍你顿好的。
我又举起手来,但是缓缓还是放了下去。
“我不打女人。但是这一次,你别想跑,你今天就是牙齿焊在一起,我也要把你撬开!我爷爷现在下落不明!我他妈根本不知道他现在是生是死,这首诗是找到他的关键!我——”我说着说着就哽咽了。
“就算你今儿是哑巴,我都要让你说话,你不说可以,但是我会用一切办法,你别逼我。这是我对你最后的尊敬!和我爷爷相比,你就是根草,你要是阻挡我,我会狠狠地踩!”我一只手抓着她领子,然后想着用什么招威胁她,我看的警匪片不是很多,也不知道怎么审讯。思来想去也没想到什么好招,没办法我叹了口气。
“算我求你好了,我希望你帮帮我,我爷爷——他虽然平常经常戏弄我,但是——我一想到他孤身在外,我就——我都不知道那个老家伙现在是不是有酒喝,我也不知道我能不能找到他再喊声爷爷。”我的眼泪不停地掉,滑落到她脸上。
我知道这很丢人,但是一想起那个老家伙,我就心酸。“我不知道这首诗到底有什么重要的!我知道的都和你说了,我根本就没有什么花招要耍的,我只要找到我爷爷!求求你帮帮我。我把我知道的告诉你了,难道你不应该把你知道的也告诉我?!”
泪水不停从我脸上,滑落到她脸上,不知道是不是我的幻觉,我看见她那火红色的眼睛里竟然有冰亮的露水。可是她咬劲嘴唇,忍着强大的感情,一声都不吭。
我激动起来,死命地摇着她:“你说啊!你给我说话!你到底知道些什么!你再不说!我真的会揍你!”我已经忍耐到了极限,举起拳头就要砸下去。
“你打啊!就你有爷爷!你打啊!我一个字都不会说!”她对着我大吼起来。
“难道你没有爷爷!你就不能想一想!要是你爹你妈有个三长两短的心情!”我举着拳头说道。
“不能!我没爸爸,我没妈妈!我体会不到!可以了吧!你们爷孙情很强大!可以了吧!”她愤怒到极点,眼角都快崩裂,竟是比我更加激动。
我的脚蓦地就是一痛,那些狗见到我压在江怜亘身上,竟然还有护主的情怀,狠狠地在我的大腿上咬。
我拿着她床头柜的台灯就往狗那边砸去。把狗驱退。
没想到手上蓦地一疼,我压着的女生,竟然瞧见空隙,狠狠地咬着我的手,根本就没有同情,显然发了狠要将我手掌咬穿。
不知道这个女的是哪里跑出来的猛兽,是豹子变的吧?我大痛之下,一巴掌抽了过去,可是她依旧不松手。
第一巴掌完全是下意识的,等到还要抽时,就硬把打人的冲动给按了下来,那手几乎已经快要被咬破了,疼到了极点。
“你是属狗的是吧!快给我松开。”
显然一巴掌把她打痛了,她眼中满是痛苦的神色,但是绝不松口。
我急中生智,赶紧把她的鼻子捏住。鼻子不能呼吸,自然要用嘴巴,那么咬着我手的嘴就会松开。
她一个劲地挣扎,死命地晃动着脑袋,我只得全身压在她身上,让她脑袋不得。过了一分钟,她终于忍不住,死命地喘气,放开了我被咬住的手掌。
手几乎被咬烂,没一块好肉,痛彻心扉,我心中愤怒急了,想着要揍她一顿好的,可是她一番折腾已经神色萎靡。其实到这个地步我们俩都已经精疲力竭。她气色灰白仿佛受到很大打击的样子,瑟缩在床脚,眼睛中的高傲不屈,很快在消褪,转眼间就好像一个充满幽怨的姑娘,那瘪着嘴巴不停颤抖起来,让人很是不忍心。
到了这个地步,再继续争斗下去已经没有意义了,我站起身来,把她放开。她的一双手臂由于我用腿残暴地压着,已经快要紫了。
我的腿被狗咬的擦去一块皮,看来来这一趟,事后还得去趟医院。这是他妈什么晦气。
我跌跌撞撞地起身,在屋子的角落找到手枪,拿起来仔细看看,我的一丝疑虑都打消了。是把真枪,而非什么仿制品。我放下扳机,看了看弹夹,里面竟然塞着满满的子弹。真不知道这女的到底脑子装的些什么,看来刚才她真的是冲着把我打成筛子的念头去的。
我把子弹一颗颗卸下来,然后郑重地非常用力地放在她床头柜上,恶狠狠地看着她,好像要把她狠狠撕下一层皮来。
她不畏惧地迎合着我的目光,同样怒视着我。这一刻对视,她的心里那住着的东西我看得很清楚。她绝对不是一个容易屈服的女人,在她心里住着一头凶猛的野兽,如果你狠,她就比你更狠,只是平常这野兽看不见罢了,但我好像还看见在她眼中看见了一个孤独哭泣的孩子。
她看着我,看着看着,嘴巴就瘪了下来,慢慢就流下了眼泪,她用肩膀擦着,慢慢从床沿坐正,然后曲起腿,旁若无人地肩膀颤抖起来。
我看了这姑娘一眼,便出了屋子。被狗咬了可不算是小事,我身上湿冷的衣服也格外地难受,我只有先去了医院。医院的急诊科医生,给我来了一针,废了我一百多块。
我跌跌撞撞就往寝室走去,湿冷的衣服已经让我头痛欲绝,刚刚在搏斗时还不怎么感觉,现在觉得走路脚都像踩在棉花上面。
路上,我拼着头晕还在思考江怜亘刚才的事情,她为什么对这首诗的触动如此之大,虽然说这首诗对我也十分重要,但我还不至于狂躁到,直接拿着枪去逼问别人的地步。
什么情况下,人会紧张疯狂到这个地步,那肯定是事情急剧紧张的情况下才可能,那么江怜亘遇到的事情,比我遇到的还要急剧?
她爷爷也给人绑架了,还留下首诗给她?肯定不会,那她顶多和我有一样的表现罢了。只有更狠。她爷爷被人杀了,然后留下首诗给她?
我的脑子越来越昏沉。
往学校走,可是门卫已经关了门,无论我怎么喊,压根没人理我,我要去摸手机,这一摸才发现,手机进了水,完全用不了。
今天是犯了冲还是怎么着,我对着大门踹了一脚,就要翻校园的铁围栏。可是做了太久的三好学生,这些鸡鸣狗盗的事情不做,竟然生疏了,翻了半天,最后栽在地上。我欲哭无泪,对着门内大吼大叫起来,什么难听的骂什么。
突然就一道手电筒的光照着我,我看不清人,只听见对方用杂碎的方言咒我还有要抓住我什么的。
我脑子一热,就撒起脚丫跑了起来。今天出门也没带多少钱,刚刚医院打一针已经让我的储蓄归零。这在外面熬夜,11月的冷风,指定得死外头,这儿我又人生地不熟,难道明天的报纸上登着,重点大学的学生不知缘故冻死街头?
我担心后面有人追来,于是穿着对面的马路,一个劲没头没脑跑起来。等我停下来喘口气,竟然已经不知不觉到了那个荷塘。
我一看见自己又回来了,眼都直了,不知道该怎么办,只是现在是再也没有力气跑了。江怜亘的房子已经黑了,但是她的门口亮着灯,好像林木工人的房子都有这样的感应灯,外面只要有人,灯就自己会亮。
灯下躺着一条狗,那狗的后腿还包扎着白棉布,估计是刚才我恼怒之下随手砸的台灯把这狗砸伤的。这包扎谁弄的?江怜亘?这女生还真是够奇怪,一边拿枪要爆我头,一边又给狗包扎,难道真的是和狗待在一起越久,就越觉得人不如狗?
这狗我还是别得罪得了,别又咬一口,还得去打针,我就要往回走。那狗却贼精,一瞧见我,立马吠声大作,吼声好像在骂我:你个***,打完医药费都不付就跑了。
我一回头骂道:“你咬我的时候你想过要给老子摊钱买药么?我也挺冤的成不,你丫再喊,女魔头就出来了!”
狗听不懂人话,说了也白说,总不能和它细细地算账,说我才是无辜的。反正江怜亘给它喂过骨头,江怜亘怎么着总归是对的,我说再多,也是混球。
我蹑着脚就要走。屋子灯就突然亮了,然后门开了。
江怜亘探出小脑袋,四处一看,看到我。我正是逃跑起手式,被她看见就泄了真气,无比滑稽地对她招手,尽释前嫌说了声:“嗨!好巧啊!”
她一脸地疑惑地看着我,接着眼神凶了起来,同时眼神中很多防备,咬着嘴唇有些捉摸不定我在干嘛。
……
有时候还真是不得不信命,刚刚还玩命地干过架,现在竟然又被江怜亘请回了屋子,两个人像是没发生过恩怨似的面对面坐着。
只是没发生过什么那是不可能的,我只能率先解释“我被狗咬了,去了医院,那医生一边挂扣扣,一边给我戳针头,打了三次才算完。出来的时候学校关门了,门卫大爷以为我是小偷,我就到处跑……”我一边说一边发抖,感觉身上好像在下雪。我再穿着这么一身衣服迟早得冻出病来,可我又没带衣服,我也不能一个大老爷们儿在她面前换衣服。
我小心翼翼地看了她一眼,她神色冷漠,好像对我浑不在意爱理不理,不过很明显,我的存在分明在巨大的影响着她。鬼知道她在想什么,女人心海底针,今天我是第一次知道。她现在做什么我都不奇怪,我猜不到她在想什么,也不奇怪。
她穿着小巧的睡衣,很可爱,脖子上被我抓的痕迹,还没消褪,看着还挺触目惊心的。
我更低下了头来,来这地方太不对了,打死都不能来这地方啊,这不是没事找罪受么?这分明就是强奸了别人,再来看看别人是不是过得很好。太诡异了。
“你待会儿,我去拿衣服给你。”
“不了,我还是回去吧?这也——没事儿,我回去吧,打扰了。”我不好意思地歉意说道。说完就起身要走。
谁知道她起身先我一步到门口把门给关了,并且钥匙从里面反锁,这一下子我算是走不了了。
这算啥?——虽然我打心眼里承认她行为模式非常诡异,但是她这么做还是又给我上了一课:一切不能以常理度之。
她对我低眉看了一眼,眼中感情太多,我瞧清的那一部分是恨意。
“我都不怕,你瑟缩什么?我要是再对你不轨,你再压在我身上啊!”她一说完,也觉得话有些不对,耳朵发起烧来。
这江怜亘我第一眼瞧过去的时候,就觉得是无双的大美女,女神中的女神级别。难能可贵的是她有一种很清澈的气质,这种气质好像是穿越了时代的民国女子附在她身上似的。
可能是女神的外表掩盖了屌丝的眼,让屌丝看什么都觉得女神好美,完全忽略女神也是人做的。
现在我决定一定要忽略她的外貌,用一个常人的眼光来看她。
她从衣柜最里面的一格子里拿了一件毛衣出来,又拿了一件休闲羊毛裤,她折好以后,然后远远地放在地上。
我拿了到厕所去换了。窗户纸都捅破了,还跟她含蓄个屁。冻死是真的,脸皮这玩意儿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
冲了个澡,穿上新装,裤子倒是真舒服,我一看还是个外国牌子,毛衣好像是手打的,穿着有些大,还算合身,老实说我想就呆在厕所不出去了,面对江怜亘压力实在太大了。
厕所很小,但是很精致,里面挂着一些女性私人用品,这个我就不细致说了。
我一出来,心情倍好,好像获得重生,一看屋里,江怜亘却不见了。我四处找了找,便大声喊了起来。
门嘭的打开,江怜亘从门外伸进头来。
“你出去干嘛?”
“厕所门是透明的,可以看见影子。”
这不前言不搭后语嘛,厕所门透明和你出去有直接关系么?什么厕所门是透明的?你敢不敢再说一遍!我惊诧之下回头看去,厕所是毛玻璃做的,压根不透明,只是在上面还是会有影子的。
她看着我一身衣服,愣了愣,神情有些悲伤,我不知道缘故,只以为在外面蹲着风吹坏了。便让她赶紧进来。
她一进来什么都没说,便将她的被子撤了一重下来,铺在地上。这是干嘛?难道这是邀请我过夜?
“诶,别别别,我还要回去呢。”
“我舍不得我给你的一身衣裳,你回去,不还给我,我会急坏的。”
这算什么话,你这衣服很牛逼么?穿着跟上了年纪似的,我才不会要。
“你给我手机打下电话,我手机落水,已经坏了。”
她把手机递给我,我随口问道:“班上老师啊,同学啊,电话你有没有?”
没等她回答,我就翻她电话薄,只有三个联系电话,一个是名字“报警”,下面的号码是110,一个是“救人”下面号码是120.还有一个是“陈教授”。
这丫头脑子烧了吧?怎么电话薄这么奇葩?我压根不记得胖子电话,每次打电话都是直接找电话薄。这下子有手机都找不着人来救我。
我把手机又还了回去。
她愣了半天,收回了手机,对着我愣愣的,好像被抽掉了魂。我用手在她眼前晃了晃。
“你没事吧?”
她回过神来“没——没有,你衣服穿反了都不知道么?”
我指着自己问是裤子还是毛衣。
“毛衣反了。”
“反了么,不是应该花纹在前面么?”
“不是!花纹是在后面的。”她笑了起来,但是笑着眼中又悲凉起来,低下头去给我整理被窝。
“很晚了,赶紧睡吧。今天的事情,我会忘记的,你也最好不要记得。”她意兴阑珊,上了床。
这他妈还会忘记,差点被人爆头了,遇上了这么牛逼的妞,是人生一绝,想忘肯定是忘不了的。
这丫头是不是还有什么话没有说?难道不应该在睡前警戒我,说:你要是晚上手脚不老实,我就拿枪把你枪毙十次。
“你不会晚上,趁机报复我吧?”我声音幽幽地道。她怕不怕我,我不知道,但是我怕她倒是真的。正常人能在干完架后还收留我一起睡觉么?太诡异了,肯定有问题。
“我不知道,我晚上梦游,说不定会掐死你,要不你也陪我一起熬夜?”她说话中透露着一丝无奈,一丝嘲讽。
这丫头还梦游,不会是真的吧?不过她的黑眼圈真的挺重的,不会是失眠吧?
“算了,你还是回去吧,我晚上睡觉不踏实,我怕到时候会说梦话。”
我都已经躺下了你让我回去?“不会吧?梦话不跟尿床一样,都是小宝宝们才有的么?”
“我一直没长大不行么?”
“那你的意思是说,你还兼着尿床?”
一个枕头迅速地砸过来。
我啊了一声。
“把枕头还给我。”
我真是被她弄得没了脾气,于是只好把枕头又还了回去。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漆黑中,江怜亘好像在看着我。
枕头上有江怜亘的香味,我抱着枕头有一种错觉,好像我正在揽着江怜亘。这个幻想太恐怖了,我赶紧把枕头还了回去。
“谢谢你收留我,这个我为刚才的事情道歉,我是因为爷爷的事情太急切了一些才变得暴躁,请你原谅。”
“我接受你的道歉。”
我草我这是客套话你没听出来么?到底谁该道歉?
我做了个恐吓她的手势,反正这么黑她也看不见。谁知道灯突然亮了,她嘟着嘴看着我,好像问我:兄台你这么做是干嘛,是抽我的起手式么?
我尴尬地放下手来。
“既然你道歉了,我就原谅你了。但是你要是跟我说了假话,你还有知道的没有告诉我——你就死定了。”
又来,又来,你拿着枪很牛逼么?
她一股碌起床,从角落拿出医疗箱,翻找出外敷的过氧化氢,还有棉签,纱布。
我说这是干嘛,解剖我?
她叫我坐下:“你不是腿被咬了吗?没包扎么?”
“医生说包扎多交二十。碰巧我金库连棒棒糖都买不起,就没包了。”
她对着我鄙夷地叹气,笑我活该,拿起棉签狠狠地蘸着过氧化氢戳我的伤口。
我就知道这丫头趁机报复。
“把手伸出来。”
我一下子伸了手。
“被我咬的那只!”她不好意思,却大声道。
“哦。”
她帮我消毒后用一卷一卷纱布,把我手缠了个结实。
灯光下,穿着睡衣的江怜亘着实可爱。末了她问道:“要是别人问起来,这手是怎么回事?”
“被人咬了啊!”我不假思索道。
她笑的很妩媚,这让我发慌,改口道:“不,是被狗咬了。”
她笑的就妩媚了。“哦哦,是被门夹的,对,是被门夹的。”
我感觉跟江怜亘一起,浑身汗毛都要竖起来,这个女人心思太难猜了,还是赶紧睡觉好了。
“我要是晚上说了什么,惊吓到你,你不要奇怪。”
“什么惊吓?”我问。
“没什么,提前跟你说一声,晚安,我关灯了。”她对着我浅浅一笑,灯光转瞬熄灭,连同她的笑容淹没在黑暗中。
江怜亘的被窝实在是很香,而且有种奇怪的温暖,我竟然一倒下被子就立马睡着了。
太阳溶溶地隐现在云层里,远远的有几只海鸥在大海上飞腾。海面平静,仿佛在静静等待日头落进海平面,尽管这还很有一会儿工夫。
海岸上,两个孩子在堆着自己的城堡,一个男子在不远处戴着墨镜在阳光下打呼噜。
女孩儿脸蛋圆嫩,戴着红色的小礼帽,穿着红色的连身裙子,娇小可爱,眉目中透露着狡黠,年纪颇小。正在细心地栽着一些植物在她做好的房子旁边。
离女孩儿颇远的地方有个小男孩搭着城堡,男孩子身上是一件大人的衬衫,衬衫直接到了孩子的脚踝,连裤子都省了。
男孩鬼鬼祟祟地靠近女孩子。
“嘿,城堡旁边不植树的!so stupid!你没有去利兹堡吧!哈哈谁叫你们老师那么boring,利兹堡,哼哼,才不是你这样的呢!”
男孩奶声奶气地说着,但是神色间的得意很是明显。他脸上到处都糊着沙子,用手示意着女孩儿看他建的城堡。
在女孩去看他城堡的时候,男孩眼疾手快哧溜几下把女孩儿的房子前的“树”(其实是一些废弃的树干)拔了个干净。
然后男孩子做了个鬼脸,撒了腿就跑了。
这地方是哪儿?我看着这两个小鬼怪纳闷的。
两个小鬼围着晒日光的大人跑了起来。
“弗兰西斯-德雷克!wake up! wake!”女孩子捉不到男孩,便去摇起了大人。
“你们两个搅屎棍干嘛?说了多少遍!叫Daddy! Do you know? ”那睡觉的男子被吵醒,装着恐吓地对着女孩唠叨。
那男孩好奇躲在男子背后问:“爸,搅屎棍是什么?很好看么?能吃么?”
那男子老大地尴尬了一下:“爱德华,这个搅屎棍呢?是中国老家的一种干农活的道具,其实呢——是形容孩子调皮捣蛋的,不能吃。叫妈妈晚上给你上上中文课你就知道了”那男子一想到好吃……就要作呕。
女孩不休,一直要抓住男孩,突然灵机一动,对着男子说道:“德雷克,He——爸爸,刚刚爱德华拔了我城堡里的树。呜呜,他是故意的,他还用力打了我!德雷克!爸爸!”
女孩子说哭就哭了,抱着那男子的脖子,那眼泪都要把男子给淹了。
这女孩子怎么看起来有些眼熟?
“Let me tell you the truth! Lizzy! 我们老师说了,只有亲生的孩子才会有爸爸的姓你知道么?你才不是德雷克的孩子呢!我才是!我叫爱德华-德雷克!”
那女孩抬起哭花的脸,大声道:“可我也姓德雷克,我叫伊丽莎白-德雷克!”
那男孩子淘气道:“得了吧,可是你的中文名字,你姓江!好奇怪的姓!我可是姓王的!德雷克的中文名字也姓王!”
“那又怎么样!”女孩子好像觉得这一点也没什么好奇怪的,好像中国名字这个东西什么的谁管他呢!
“看着好像没什么问题,但是中文名字,你和德雷克不是一个姓!所以你还只能算半个孩子,而我才是德雷克真正的孩子啦!是不是?爸。”
被他们唤作德雷克的男子,简直被这两个活宝闹晕了。
“我要告诉你们的妈妈,说你们现在为了争夺爸爸打了起来!”德雷克摘下墨镜,满是无奈的说着。
这个德雷克,中年男子,尽管脸庞晒成古铜,但是分明瞧得出是个黄种人,眉间那种中国人的豁达还有无奈,怎么都被阳光晒不掉。
俩孩子为了争正统斗起了嘴。
“你是德雷克捡的!”
“才不,你是MS德雷克捡的!”
“呸!”
“好啊,你竟然用中国口水喷我!”
……
太阳快落下去了。德雷克把两个孩子背在地上,左边肩膀一个,右边肩膀一个,他一个脑袋两个大。
“哼哼!爸爸有话要说!你们俩小家伙都安静一下!爱德华,你这么样欺负姐姐是不对的!弟弟要尊重姐姐!”
“就是,他哪里有个弟弟的样子!”那女孩子听了十分消气。
“还有Lizzy!你知道我为什么叫你Lizzy么!因为在一本名著里,Lizzy是一个顶好的姐姐!可你看,你都不让让爱德华!姐姐和弟弟窝里斗怎么成?姐姐是弟弟的僚机,知道么?弟弟是姐姐的小棉袄!你们这完全违背我生你们的初衷!”那德雷克看起来非常悲凉,好像当初应该把他们射在卫生纸里。
爱德华抓着他爸的头发“爸,难道lizzy真的是你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