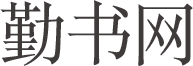第二百三十五章
“我擦,你敢打我?”我瞪大了眼珠子要还手吓吓她,这丫头没等我胳膊抬起来就一个侧身一脚伸到我腿后,只手横在我胸前一使劲,在她迷人的笑容里我就被她绊倒了。大林捂着脸要上楼去,“你回来!你们海哥让我来传话的!”
大林一听立马笑脸相迎,“不早说!你来这么早肯定没吃饭,我这就给你买早饭去,稍后再细谈。”
“嗯!去吧……”这丫头虽然答应着大林,可是眼珠子一直没离开过我,那双杏眼还真让我没脾气。
我很无奈,又不能动真格跟她干一架,橙子却在旁边笑眯眯的看着我,“我可得把这事记清楚,等肖宵来了就跟她报告!”
橙子这家伙真够无耻的,不过说到眼睛,肖宵的眼睛比眼前的这丫头可漂亮了上百倍,比她大而且又亮又黑,睫毛都比她长。想到肖宵我也就没有气了,我站起身来一拱手,“师太,你到底想把洒家怎么着啊?”
一句话让她扑哧一下乐了,眉笑眼开的,在她鼻梁旁边有一颗非常非常小的痣,笑起来时痣已经没入皱纹里了。笑了几声转而又板着脸说:“我先去洗头,你这事还没完啊,在这侯着吧!”
等她上楼以后,橙子问我她从哪冒出来的?长的还挺漂亮。
我又怎么会知道,先等着早饭回来再说吧。过了一会儿,店门处有饭香飘了进来,大林淋着两手早餐吆喝着“吃饭喽!”
“包子?”我拿起一个就塞嘴里了,“嗯,这个好吃。”
“咚咚咚”下楼梯的声音,一阵风在我身后刮起来,看橙子的眼睛就知道那妹子下来了。我一转头,那妹子把没干好的头发甩起来,湿漉漉的都搭我脸上了,“我擦……你这欺人太甚……”我蹭的站起来了。
那妹子也不含糊,一抄手就把我的椅子抽走了,安然的坐在那儿了。
气氛有点紧张,大林拍拍手道:“各位都是自己人,大家先互相认识一下。这位姑娘是卞京的妹妹,卞子毓,是个响当当的女人物。”大林又指着我和橙子说,“这两个是海哥的侄子,魏雨缪,刘橙。”
“你好!”橙子第一个站起来握手。卞子毓点点头,很开心的打了声招呼,对我倒是没有一句话,视我不存在。
大林接话问她“海哥有信了吗?”
“嗯!”卞子毓吃了点油条,喝了杯豆浆,很淑女式的泯了下嘴角,“海哥说三天后启程,飞去甘肃肃北蒙古自治县,他们在那里等你们。”
“我擦,那么远?我们怎么去?”橙子一高跳起来。
“都是为了你,你还嫌远?”我抓起一个包子就扔他脸上了。
“你就是那个中了咒的家伙啊?”卞子毓摇着脑袋,围着橙子转圈看,又撅着嘴说,“我以为是那家伙呢?”这妹子又失望的看着我。
橙子嘴快,话都没过大脑,想都没想脱口而出,“他?怎么可能,他可是有「鬼……」”
「摏」字还没说出口,林霖见机打断他,“有鬼缠身?你就是到处乱跑才挨了一下子,否则也不会这样了。”
橙子冷静下来,意识到了问题,马上改口说,“这下是我被鬼缠身了,哎。”
卞子毓只是觉得我们三个奇怪,也没有去多想,她吃完早饭,抬腿走人。
望着她纤细的身段消失在远处,我们三个都呆住了,橙子说这是他见过最漂亮妹子,见我笑呵呵的看着他,他又改口说可惜还是比不上肖宵。
只有大霖的神情比较冷峻,看到卞子毓上车走远以后,立即让我和橙子收拾行囊,当天就启程。
我俩被他催促着忙活了一上午也不知道为什么,大林说没有特殊情况二叔是不会让别的组里人带话的。
既然传话过来,那就是件紧急事情,而且不能耽搁。
为什么不打个电话来?大林说这里的所有电话都已经不安全,隔墙有耳。
当天下午我们就背着简易行囊出发了。
雨瑶看着我们几个忙忙碌碌的跑出店,就再也没回来,也打过电话,可是我们都关机了。
我们大半夜才飞到敦煌,就在机场附近找了个住处暂时歇脚。
这里的环境卫生还不错,等我们纷纷倒下去准备大睡时,林霖又发话了,明天得有心里准备,会有一两个小时的车程。
我们现在已经进入事件现场了,不能在迷迷糊糊。他还说了一些,可是我都没听进去,早就呼呼大睡了。
凌晨五点准时被闹钟吵醒,大林一改往日的懒散,事事先做,动作麻利,跟平常简直判若两人。
收拾完以后随便吃了点早饭就发现有车开到我们跟前,车窗摇下来,一个戴墨镜的秃头看着我们。
我是迎着阳光看他的,一下子在我眼前出现了两个太阳,其中一个就是他那光头,简直又大又圆。
橙子说这货是故意来找茬的吧。
我说我们还是快吃饭,吃完了就走人了,这货要是真来找事的那就修理他一顿再跑,反正车里就他一个人。
那个墨镜光头倚在半开的车门上,呲溜呲溜的吸着袋装牛奶,眼睛越过镜框上缘看着我们几个。
大林头也没抬,也不知跟谁说了句“等我吃完。”
我擦,我和橙子同时停下咀嚼的动作,鼓着腮帮子一齐看着林霖。
他倒是淡定的很,低头喝着粥,抬手指着大光头说“他是海哥的人,待会他带我们走。”
我们泪流满面,二叔真是周到,特意派人来接我们。
我们在公路上驰骋,司机就是那个大光头,他说他和姚明一个名字,橙子摸着他脑袋说,没看过个子这么矮而且还是光头的姚明,这胖子就嘿嘿一笑。
人比较随和,也挺有趣的。我还打算让他带我们看看敦煌石窟呢,可是这家伙却说这得听海哥的,海哥说怎么办就得照做。
这一路前半段还比较顺畅,柏油路铺的不错,可是后半段就不行了,全是泥土路,只要一跑起来,沙尘暴似得尘土全呛进车里了。
不知道行驶了多久,当我无心的看着窗外时,竟然看到了雪山,“快看,有雪山!”我和橙子挤在窗口,张大了嘴。
巨大的山体魏然耸立,尖端没入云层,烟雾缭绕,山体通体雪白,银装素裹,连绵起伏的山脊像巨龙卧俯,一座座冰川排向天边。
姚明说这里是祁连山脉的北段,前方会有更大的冰川群。我们更加兴奋,毕竟从来没见过这么气势磅礴壮阔的自然环境。
我们的车在它的脚下,就像是我们在看脚下的蚂蚁的一样,在大自然的面前,我们人类是那么的渺小。
终年积雪使得贴近山体的一层冰雪变得坚硬无比,冰甲挂身的冰川巨人静静的看着我们在脚下疾驰而过,而我们只能仰望它,却看不到它的全貌。
我们要去的地方是一座叫透明梦柯的大雪山,在老虎沟的地方,姚明说二叔就在那里等我们。
在看其他的雪山同时也幻想着透明梦柯会是什么样?姚明就说了一个字,大!
车子开始了颠簸,有点倾斜,爬过了几道低矮山坡,来到了一处平坦开阔地带停下了,终于到了目的地了。
兴奋的心情还没平息,刚跳下车,阳光从四面八方温柔的包围了我们,通过山体冰雪的折射,身体更加的温暖,踏到实地后感觉一阵凉气漫过脚面。
这里比地平面高了几十米,温度比较适中,并不是太冷,之所以感到凉意可能是自我感觉。
二叔带了几个人从附近的一处帐篷里钻出来,跟我们打招呼。
十几个人就围了起来,互相认识了一下。
这些都是二叔的人,大霖和他们比较熟悉,主要就是介绍我和橙子。
可能他们知道我们与二叔的关系,所以这些人对我们两个比较客气。二叔吩咐他们准备行装,明天预备登山。
我们所处的是山体延伸出来的一块向阳的地方。
二叔带着我俩在附近转了转,指着不远的山地说,那里就是透明梦柯,它是蒙古语的音译,就是大雪山的意思。
绵延两千多公里的祁连山竟然能孕育出这样壮阔大气的山体真是不得不感叹大自然的力量。
大雪山是祁连山北端最高的山体,由于地处西北气流直下的要冲,高山降水丰富,因此孕育了多达二百条的冰川。
这里的海拔不是很高,只有四千多米,所以登山者不必担心高山反应。
这里的山脚下一般都会有一些登山的大本营,为了安全起见,我们和他们分开安营,毕竟我们来这里的目的不同。
第二日,登山装备已经差不多了,我们一行人有两个大型帐篷,在这里只要留下一个人作为我们下山的接应,其余人都要上去。
我和橙子看着眼前茫茫雪山,半山腰处就开始有冰雪覆盖,实在有点高,我自己都不相信自己会爬上去。
姚明跑过来给我登山用的绳索,笑着说,大家都一起走,很容易上去的,这里又不是喜马拉雅山。
我和橙子是第一次干登山这事,二叔也为了我们安全,决定用绳索缠住我俩,和别人拴在了一起,这样就不怕个别人出现意外了。
我们开始准备,毕竟和其他人不太熟悉,所以大霖主动在我们前面带着我们,我在倒数第二个位置,最后一个人是姚明,这家伙说他比较胖,一旦有个闪失能起到抛锚的作用。
二叔和其余几个人都在前面,我们制定的计划是登山五个小时后开始进食进水,当遇到第一道冰雪山地时要安营扎寨,当天不在前行。
临行前,二叔带着众人在营外烧香祭拜了一次,据说我们这种人来了会搅扰到山婆婆,祭拜就是为了告诉她,我们不会去打扰她,同时祈求她的庇佑。
祭拜完毕,留下一人在山下,其余人陆续换上专门的登山服,戴着手套和避风镜。
一行大约十四个人,除了我和橙子,其他人还都很壮实,绝对都是干体力活的好手。
前半段路比较容易,坡度又比较适中,因此行进速度也就加快。
另外,姚明时不时的跟我们聊天吹牛,我们也并不觉得累。
橙子经常回问他,“大明,那天看到我们时,你对我们的第一印象怎么样?”
姚明嘿嘿的笑着说:“就觉得你俩不是什么好货,要不是大霖在你俩旁边,我都懒得去搭话。”
“我擦,我俩的印象就那么差啊?”橙子故意用脚踹了些石头下去。
“轻点嗨,我还在你后面呢。”
我没怎么听他俩说话,一直在想着问题,二叔说这次主要是因为有了泪冢的确切消息才来的,可是语气中竟然透着兴奋,好像比我们还要高兴。
我就不相信,我们十多个人来只为了橙子一个人?
如果没有五人会的关系,那么泪冢的消息又是从哪得来的?我越来越觉得这一次寻找泪冢的事绝非他说的那么简单。
第一天就走到了冰雪地带,整支队伍也就停下来做休整。
我们在一处巨石凸出裸露的地方扎营,这次又是两个营帐,不过比山下帐篷的小了很多。
半山腰处虽然树林茂密,可是到了晚上依然会有强风,所以找适合过夜的地带最好是安全稳固的岩石背后。
在山里过夜又不是第一次了,除了有些零星雪花从上面飘下来外,在没有能让我们开心的事了。
营地周围起了两堆篝火,一时我又睡不着,便起身走走。
在营地周边的林子里晃悠,看着夜空里的星星眨眼,听着静夜里大自然的声音,俯身望着山下是一片林海,在风的作用下发出立体而厚重的喧哗声。
溜半天想回去了,一转身刚刚熟悉的山林却已面目全非,到处是破败倒下的树木以及动物的尸体,刺鼻的血腥味弥漫在林中。
我这是走到哪了?
我有点慌,不过清楚的意识到眼前的山林绝不是自己刚刚路过的地方。也就在我转身的瞬间,这里已经发生了变化。
有人在哭?悲切的哭声丝丝缕缕,断断续续,哭得我心里起了恐惧感。
这是人在哭?还是动物?我不想跟着哭声走,可是自己却正在向着那个方向去。
我拍着脑袋心想不会又是鬼摏在支配着我走着呢吧?应该不是,我没有看到另一个一模一样的我存在,所以鬼摏应该还在睡觉呢。
哭声是从一个树洞里传出来的,我找到了它。
大树连根撅起,粗壮的树干中心已经空空如也,还有一半埋入了泥土,哭声就是从那里传来的,幽幽的黑暗树根让我止步不前,而哭声也越来越清晰。
我目测了那个树洞,弯腰就可以钻进去,可是进去了我要干什么?
我转身要走,迎头碰上了一个软软的东西,竟然是一个老人,老太太被我撞得要后倒,我赶紧伸手抓住她,可是她还是倒向了后面,而我手里抓着的却是一条已经断了的胳膊,我呆在那里了。
深更半夜,深山老林里,怎么会有老太婆?
老人又站了起来,虽然没了胳膊,脸上却还带着慈善的微笑。
她没有嘴唇,森白的牙齿翻露在外,一副皮笑肉不笑的神态,眼睛直直的盯着我,那种眼睛是我见过的,当妖瞳出现的时候周围生物才会没有瞳孔。
难道这里还有妖瞳?
我在一步步后退。我没看清她是怎么走到我跟前的,也就是一晃眼的功夫,拉着我的手说“跟我来?”
由于她自身的摇晃,我发现她的脑袋都在左右摆动,摇摇欲坠的样子。
这肯定不是人,我已经可以确信这一点。
树洞已经张的大开,比刚才的还要大,埋入地下的部分比裸露的洞口更大,一脚踏上去就像是流沙,越陷越深,而那个老太太就在外面笑着。
我大呼大叫,最好让周围的人都听到。
呼啦一下子,两团篝火然起来,照亮了整个林子。
橙子正捂着宽大厚实的棉衣看着我,“你瞎嚎什么?把我们都吵醒了。”
二叔也跑来了,问我是不是做噩梦了,山上气压低,容易出现幻觉,大林递给我一瓶水让我冷静一下,我想把梦说出来,可是到了嘴边就想不起来了。
“大家都睡吧,已经没事了!”二叔把其他人安顿好后,就让我好好想想到底梦到了什么。
因为他知道我身上背负着鬼摏,在这里做了噩梦肯定是有什么预兆的。
他私下里跟我说,这整座雪山都有可能是泪冢的影响范围,所以只有我的预感才会对他有用,橙子,大名,林霖都围拢过来。
我惊讶的看着周围的人,他们的脸是那么的模糊,我伸手触碰他们,怎么是黏黏的感觉?
他们的皮肤在吞噬着我的手指。
每个人都挂着邪恶的笑容,可是却带着哭泣的腔调说话。
他们已经不是人类了,几双手逐渐的伸向我,“快说啊,雨缪,刚才你都梦到了什么?”
“走开!你们不是人类……”我使劲格开他们手,慌里慌张的爬起来就跑。
腿脚被绊了一下,一跟头摔出去趴在大石头上了,一模脑袋,好家伙都是血,可是不知道磕在哪了,我生出来的这些血容易吗。
我心里很乱,冷汗冒出来了,就比水龙头的流速慢一点而已。
我本想用手撑地站起来,可是无处下手。
全是流沙,不知道从哪冒出来的,低头看到胸口下面的流沙开始下陷,一圈很小的洞口在逐渐的扩大,等到所有的流沙陷下去后,一个无比空洞的坑出现在我身下,有热风从里面吹出来。
我双手紧抓着坑边缘的石头,两脚支在坑边,这是非要把我往坑里骗啊?
坑的宽度让我断了翻身越过它的想法。手开始颤抖,发麻,没支持住,大头朝下就栽了下去。
坑有点深,十几秒后我到底了,前面已经没有路,倒退着回到洞口已经不可能,这里很窄,根本无法转身,只有挪一只胳膊的空隙。
空间狭窄,空气流通就成了问题,气流越流越慢,再加上我大头朝下,呼吸就变得很困难,闷热感加重,头重脚轻,双手还得支撑整个身体的重量,“快来人啊?救救我?”
虽然知道声音不会传的很远,可是心里还是抱着一点希望。
这一切变化的太突然,是不是所有的人都变了,难道从一开始我就被他们骗了吗?如果能出去,我是不是该逃下山。
我能看到脚下的星空,确切说是脚底以上的星空,因为我是倒立着困在了深坑里。
然而一颗歪歪扭扭的脑袋遮住了星辰,锐利的目光刀锋一样的刺激着我的视神经。
“你是谁?”我闷闷的问它,说一句能喘三口。
它只是笑。
没有嘴唇的笑容很可怕,一道钩子从左侧嘴角向上划,整张脸皮都被扯了上去,露出底下鲜红鲜红的嫩肉。
那张皮飘在空中缓缓落下,他妈的,直接落在了我脸上,这可不是什么好事,那层皮在我的脸上开始缓慢蠕动,一点点的收缩。
“啊……!啊……!”我拼了命,喊破嗓子的大叫,
“啪!”的一下子,我后脑勺被人抽了一下,我睁开眼发现竟然是二叔,“你鬼叫什么?把大家都吵醒了?”
大林从侧面递给我一瓶水让我冷静一下,接着就是橙子,大明都围拢过来。
这情景和我刚才经历的简直一模一样,这是怎么回事?这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
我还没等他们伸手,就跑出去了,也是同样的地方摔了出去,也是满头都是血,我内心骂着“这他妈的是怎么一回事,简直就是梦境的复制版啊。”
橙子他们正往这边赶过来。
“别过来!一个都别过来了,让我静静。”我趴在地上,等着流沙的出现,脑子里乱成一锅粥了。
就这样过了几分钟,流沙并没有出现,身下也没有洞口,我也能爬起来。
我警惕的看着周围,不远处二叔几个在看着我,他们身后是走来走去的几个人在撩拨着篝火,天空已经变得浅蓝,清晨的气息正加速袭来。
渐渐的二叔他们脸上出现了柔和的光,清晨的第一缕光线照射着我们。
他们关切的神色让我醒来,恢复了常态,我明白新的一天已经来临。
我疲倦的看着身边的人忙忙碌碌。
早饭我吃的很少,我在想着昨晚的事情,别人不明白为什么我独自一个人在角落里啃着压缩食品。
我把爷爷曾经留下的书再一次翻开,我记得里面有一篇记录了些什么。
后来终于找到了,对,就是它。
在这座雪山里并不是只有「泪冢」存在,同时还存在着另一只明魅,「永梦」。
看完书,我了解到一些关于明魅「永梦」的事情,只是不清楚为什么会在这里遇到它,而且偏偏是我碰上了它。
「永梦」的特点是它会把你拖入梦境中再也不让你醒来。
每当你要打破梦境的时候它就会立即制造另一个梦境来禁锢你,永无止境的假象会让你疲于奔命,对于人类来说精神会永远停留在梦里,躯体会安然无恙的躺在现实世界。
在它的势力范围内,无论是谁都很难逃脱它的梦境,除非它只是调皮逗你玩。
我之所以能清醒过来,也是因为它放了我一马。
书上说,「永梦」的力量其实很强大,目前它是所知道的明魅中唯一一只可以与暗魅分庭抗礼的。
虽然力量强大,可是它并不像暗魅那般阴险狡诈,「永梦」比较喜欢干净简洁,有温暖柔和光照的地带。它也是大自然里最爱搞恶作剧的魅,因为无法与之抗衡,所以大多数的魅都成为它戏耍的对象。
据说,它非常讨厌魅的死亡,一旦看到了魅的消逝就仿佛看到了自己的结局,它也很快就会彻底的消失。
也就是说,只要有「永梦」存在的地方,是肯定没有死亡的。
一般情况下,它不会对人类制造虚拟梦境。
为什么会对我产生了作用?这可能是因为鬼摏的原因。
我仔细的想了昨晚的梦,其中一部分应该是鬼摏给我的提示,每次有魅出现时我都会收到一些暗示,这次也不例外。
第一个梦里的我陷入流沙中和第二个梦里简直如出一辙。
这一点可能就是鬼摏给我的暗示,而除此之外都是「永梦」制造的虚假梦境。
我在梦里的时候,它并不认为我是人类,而是暗魅鬼摏,所以才让我三番两次的陷入梦的循环。
当鬼摏不在给我暗示的时候,也就是恢复了我人类的精神世界时,「永梦」也就看清了我是人类的本质,所以并没有在梦里继续缠着我。
其实想来,还是很可怕的,我想知道有没有植物人是「永梦」造成的?
“准备走啦,你还发呆啊?”姚明跑过来拍拍我,“你这第一晚的雪山夜看起来很失败啊。”他摇晃着帽子又转身走了。
我想告诉他,那顶帽子实在太小了,他的半个秃瓢脑袋都露在外面。
第二天的行程很艰难,毕竟要过冰雪地带,冰层很厚又很滑,从山谷里吹来的风还带着很多冰雪碎沫,这一切都延缓了我们前行的速度。
同时为了避开其他登山者,我们走的又是比较困难的雪山北侧。我和橙子是盲目的跟着爬,在这一行队伍里,只有二叔大概知道泪冢的位置。
他之前跟我说过,泪冢应该是冰雪之源,所处极冷之地,它应该藏在山体内部,而不是表面,我们要找的恰恰就是进入山体内部的缺口。
山势开始变得陡峭,我们都是一步踩实了才会迈出第二步,借着身边能固定的东西往前挪。
从山顶吹下了一大团的雪沫,裹挟着细碎的冰凌拍在脸上就像一盆仙人掌迎面罩你脸上一样。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是半山腰,这里已经密布着冰层,还有大团大团的雪花带着阳光一起飞。
这里的气候反复异常,二叔警告我们不要大声说话,刚说完,橙子就来了一个响亮的喷嚏,由于山川回音增加,有个巨大的雪块在身旁滚落下去。
我们吓得全都禁了声,橙子硬生生的把连续的喷嚏憋在了嘴里。
我一边爬山一边合计着「永梦」,它不像鬼摏那般暴力残忍,它只是愿意和任何动物开玩笑。
如果有人主动招惹了它,它也只是作弄你一顿后就消失的无影无踪,不再出现,虽然它拥有强大的力量,却没有借以为非作歹。
也许魅也分善恶,和人类一样,它们是可以和人类并存的群体,在古往千年中没有交集,没有兹扰,大家相安太平。
具体的魅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进入人类社会了已经无法计算了,这可能和人类无度利用自然资源有关系。
如果别人破坏了你的家让你流浪,你会怎么样?
正常的人类内心会有仇恨,会去报复,同理,魅群里有一部分也开始了报复。
「永梦」不是报复人类的魅,它选择了逃跑,逃到一处它喜欢的地方住下来,过阵子在逃到另一个地方去。
它习惯了流浪,就像人类的旅行者,从来不停歇,一生中都在用脚步丈量着世界。
我开始对「永梦」报以好感,起初被它戏弄也属无奈。
那个梦的前半段应该是鬼摏造的,我一直是这么认为。
我们在找明魅的时候,鬼摏也在找,只是我们的目的不同,它是为了杀戮,补强自己。
这一次也是对我的一个挑战,自从上次对付妖瞳的时候,鬼摏占据了我的意识把我踢了出去后,我就开始担心有朝一日鬼摏会不会彻底控制我?
每一次大魅出现的时候,它都会在我的脑子里跃跃欲试,就像一头怪物要穿破我的身体去毁灭眼前的一切,我已经开始讨厌鬼魅。
在我们休息的时候,我告诉二叔在这透明梦柯里有「永梦」。
二叔只是愣了一下,随即眼睛里闪烁着了欣喜的光芒。
他搂着我肩膀,低声细语的告诉我:“这事可别乱说,谁都不能知道。”他站起身,警惕的看着周围,再就没说话。
我们在一处松衫树下定了下一步的计划,十多个人静听着二叔的决定。
下一步行程可能会更艰难,我们要找的是一块半透明的山岩,那里才是我们的接下来的目的地。
我们需要借助山岩进入到山体的内部去,泪冢就在山体中。
这下目的明确了,也不乱了。
不会像个傻子似的跟着二叔走了,至少我们都知道了目的地。
我估计其他人也是这么想的。
之所以没有把这些提前告诉我们,可能有两点原因,一是担心走漏口风;二是怕这些人半路打了退堂鼓。
现在我们所在的位置即使想打退堂鼓都回不到山下了,除非搂着雪崩下去,又快又省力。
二叔安排人准备了开山铲,这种铲子很小,一般都是单手用,铲的前端是个圆润的钝角,铲面整体则是冲浪形状。
三五个人从背包里抽出几柄铲子,检查一下铲子头是否牢靠。二叔打算明天继续下一段行程,在那之前他得先去查勘地形。
我听了以后就担心他,“那你得小心点,多带几个人去。”
“这种事我经历了多少年了,没什么可怕的!”二叔点了三个人就出发了。
风起了。
他们消失在雪雾里。
我们得解决当天晚上的住宿问题,于是剩下的十二个人开始凿雪。
我们挖了很大的一个雪洞,洞很深,用冰块树木支撑四壁,我和橙子主要负责搬运,把他们挖出来的冰雪都堆在附近。
其他十个人专门负责洞的设计,这可是有点技术活,大霖说冰层的厚薄不一,一般不能急速下挖,同时还的合理分散上层的压力,否则很容易被埋进雪窟。
等雪洞挖的差不多了时,二叔他们回来了,风雪里却只有三个人影。
我明明记得去的时候是四个人啊,一时间我们都预感到不妙,肯定出事了。
三个人艰难的爬过来,二叔一把摘下帽子和脸罩,一副铁青脸色,不知道是冻得还是气得。
他抡起胳膊就把帽子面罩摔在了地上,使劲的踏了几脚,把帽子踹进了我堆起来的雪堆里。
“海哥!”
“海哥!”
我们都围了过去,大明把深陷雪堆里的帽子抠出来,拍掉了雪递给二叔,“海哥,出事了我们担着,你别生气!”
二叔像头野兽一般猛然间回头,“你担着什么?你能担得起别人的命吗?”
他的眼睛狠狠的盯着大明,双手揪着他衣服,领子收缩起来边缘已经勒进了大明的粗壮的脖子里。
大明原本就胖,脖子肉比较多,再加上海拔高度,原本呼吸就费劲的他此时更加难受。大林一把拽开二叔,“海哥,冷静点!”
我和橙子扶着大明,“怎么样?没事吧?”
大明咳嗽几下,摆摆手,“没事,这算什么。”
他张大了嘴兀自喘息着,额头渗出冷汗来。
二叔一副乌青乌青的脸色,叼着烟,眯着眼睛看着远处被云层遮盖住的山峦。
他一动不动的立在那里,任风雪扫射着胡子拉碴的脸。
有人让他躲到洞里休息去,他没动也没反应。
整体气氛冻僵了,都愣在原地,我们也不知道二叔他们出了什么意外,只是看到与他同行的另两个人脸色也很不好,只是不住的摇头。
大林在二叔耳边低语了几句后,跟我们挥手让我们先进洞去。
天色已经开始变暗,据有经验的人说,晚上可能会有大雪。
洞口是倾斜走向,侧面有滑道还有凹坑,坑里洒了一些碎石子。
那几个不认识的人说这么做是为了进出洞方便,总不能滑得下来,爬不出去吧。
我试了几次凹坑爬上爬下,起脚使劲都不打滑,挖洞果然是个技术活。
大林还在外面并没有进来。
我们这些人就凑在一起听另一个与二叔同行的人讲述他们这一路的情况。
橙子的情绪一直很低落,可能是觉得死了人和自己多多少少都有关系。
大明看着他瘪着嘴说:“我们来这又不是为了你,只是顺便带上你而已。”
其他人不明白,问怎么回事?
于是橙子把自己中了摄食咒的情况说了出来,其他人发出很长的一声“哦!”
一时间气氛缓和了许多,他们七嘴八舌的开始说,这次主要是五人会的行动,没想到还可以帮的上橙子的忙。
另一个人就开始说他们今天趟过的路,以及如何死了一个。
他们都叫死去的那位小川。
二叔他们四个人爬到一处从山体延伸到半空的崖口处,二叔说那个入口就在崖口的下面,贴近山体凹陷的地方。
崖口那里是一个天然的积雪平台,上面有稀松的雪层,路面也比较滑,他们几个用冰镐扣住崖面上的冰,用安全绳索以及升降器下滑到崖下,贴着山体左右移动。
他们四个人有四条绳索,并排滑了下去,每个人负责在自己的一块区域找寻透明石头。
二叔看了看表说再等个半小时,太阳光会照射过来,那时候就能分辨出透明石。
可是意外就发生在这半小时里。
起初,他们悬在半空,有说有笑。随着时间一点点的推移,却等来了更大的危险。
雪山上最危险的事情可能就是雪崩了,可是他们却遇到了比雪崩更可怕的事。
二叔发现他们面对的山体表层有多处划痕,而且时不时的有划破冰层的声音,这不是登山镐造成的,而像是一种动物踏上去产生的。
大家都听到了这声音,只是还没有头绪。
忽然间,几个人就身不由己的开始晃动,他们慌了,在这种高空作业最惧怕的就是左右摆动,而且有东西在影响着他们,不知道有什么东西在周围,他们看不见,而它确实存在。
四个人在半空中的剧烈摆动导致绳索顶端出现脱索现象。
他们完全没有着力的地方,时不时会撞到一起去,像小孩子在荡秋千。
我们听了都微笑着,而叙述的那个人接着说了句话让我们无法理解,他说可是当时根本没有风,一点都没有,如果有风的话也不可能降下崖去。
没有风?四个人却悬在空中到处乱摆?
他继续说,感觉自己是被一只无形的手在推着,自己的摇摆方向完全不受控制。
他当时还听到耳边有个声音,只是不确定,也可能是气流在山间回荡造成的。
总之,四个人就像是被人操控的玩偶,随意的丢来丢去。
再不想办法回到上面,就很有可能掉下去。
几个人的心里很慌,而小川在这时更是大喊了一句“我要脱索了……”小川的绳索在崖口平台上固定不牢,来回的摆动使绳索固定钳出现了松动。
二叔离他不远,一边让他冷静,一边对他说:“上我这条来……荡过来时候你就松手跳,我在这边抓住你。”
雪白的峭壁前,两个人试了好几次都失败了,每当两人摆动到距离最近时,小川都没有勇气跳出去。
毕竟,脚下是白茫茫的一片,一旦离开了绳索心里也就失去了依靠,可是不跳出去就只能给自己的生命倒计时。
由于刚才的喊声造成顶端松软的积雪出现松动,它们像细雨一样稀稀拉拉的落下来。紧接着天空变暗了,巨大的黑影笼罩在峭壁上,包围了他们四个。
他们不约而同抬起头来,看到至少十几吨重的积雪大面积堆积在半空中,就像有东西托着它们一样,积雪悬在我们头上,并没有砸下来。
我们都以为是山婆婆保佑着,可是好景不长,那团雪突然失去了承受力,就像一块被抽走托盘的蛋糕,瞬间就拍下来,它们是斜着落下来的,大部分砸向了小川那边。
情势急转直下,小川知道再不跳就来不及了,闭着眼睛就跳向了二叔那边,可是雪崩发生时他俩并不是最近的距离。
二叔措手不及,奋力的伸手去抓他。
整个人只有腰部是被绳索缠着的,后来他倒吊着身体总算抓住了小川的手腕,绳索以及雪涌大面积的滑下去,迎面冲击着他们两个人,下落之势气势汹汹,将他们瞬间吞没。
常人的话恐怕早被冰雪撞得松手了,不过二叔还是死命的抓着小川。
他想等雪势小了以后在想办法,可是自己不知道自己都危在旦夕,排山倒海的雪浪已经把他身上的绳索冲开了,他只能徒手抓着升降器,另一手紧扣着小川手腕。
其他人完全被这突然袭来的大雪冲击得晕头转向,全都是伤痕累累,衣服面罩已经破了,脸上到处是血。
看着二叔自身都难保,在这么僵持着两个人都得完蛋,小川说了最后一句“替我去看看我母亲。”
随后扒开了二叔紧握的手,带着笑容坠了下去。
这些人眼睁睁的看着他坠入到下面的云端上又消失。
二叔一直保持着抓人的动作,僵了很久很久。
其他人看到雪层落下后,就唤醒二叔,依靠山体的凹凸面支撑着,他把小川原来的绳索甩向其他人,这样众人才利用升降器把他拽到崖上。
我们听完都觉得这是个意外,可是二叔并没有这么想,一路上他都虎着脸。
因为绳索的原因使得那声大喊带来了巨大的灾难。
在积雪厚重的雪山上,确实不易大声喧哗,更何况在那种凹陷的山体悬崖处,那里的回音会将原本的声音强度扩增至上百倍,雪层虽然厚但是并不实,更容易导致雪崩。
我们在雪洞里过了一夜,洞内还是很暖和的,比露天营帐好多了。
二叔一直都在外面,大林给他在外面安了野外帐篷。
我们这里是雪山北段,地势比较陡峭,山风强度也大,即使专业的野外帐篷住着都会提心吊胆的。
所以我们才挖了雪洞,用砍断的老树固定在洞口,防止一旦大雪盖住洞口就不容易出去了。
早晨醒来,我们化雪烧水,所用的装备一切齐全,看来,负责采购物品的人一定是个行内人。
等我们出了洞,就看到二叔坐在他的帐篷外吸着烟,一轮红日刚露出地平线,红色光线渲染着东方。
我过去给他一杯热水,拍拍他肩膀,本想安慰几句,却没开口。
整支队伍的气氛被二叔影响着,大家都没有笑脸,只有我和橙子私下里能说几句,寂静的早晨没有了生气。
打破沉默的还是大林,他让我们把帐篷拆了收拾起来,各自的攀岩手套,冰镐,还有绳索等等都归纳到方便取出的位置上。
一行十五人背上大大小小的包,聚在一起,等待下一步指示。
大林跟二叔耳语了几句后,就立在那不动,等着二叔发话。
他不紧不慢的站起来,喝了一口水,我看那杯水都快结冰了。
“今天要以安全为首要目标,全程禁声,到了目的地在布置下一步行动。我们现在站在这里的一共有十五人,我希望回来后依然还是这些人。”
他有气无力的说着。
“海哥,你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就算出了事做了鬼,也绝不会去为难你。”大明亮开了嗓子。
其他人也都齐声响应,“我们跟着海哥做事原本就没什么怕的,我们都有一条命。海哥,就等你一句话了。”
“嗯!”二叔深深的点点头,让大家对准时间,半个小时后出发,由昨天的三个人在前面带队。
橙子跟我说:“二叔还真是个土匪头子。”
风不是很大,我们排着队走在雪山北侧,山影笼罩着我们,一排排雪松成为我们攀爬的助手,深一脚浅一脚的前进着,还能看看周围的景色。
我和橙子的心情大好,时常指着自然奇观惊叹不已,在我们身后的大明看了直摇头,“你俩是不是从没出过家门亲近大自然。”
前方传话过来说小心雪下有冰窟窿,让我们踩踏实了再挪步。
我们这边也很给力,刚回答完人家明白了,就“扑通”一下陷进了无底深的冰窟窿里。
我和橙子双双沉下去,当时我们就慌了,双手在雪里胡乱抓着,也没敢大声嚎叫。
我眼前全是雪,感觉被雪活埋了。
幸好我们俩前后是大林还有姚明,一个伸手敏捷,另一个墩实大气。
他俩使劲扯绷直了绳子,我们也就露出了头来。
“我擦,吓死我了!”我大口喘着气,橙子也瞪着惊慌的眼睛四处看。
所有人都停下了,等确认我们没问题了才开始走。
大明说我俩就和那变魔术一样说没就没,等有空时教他一招。我俩把裤子上的雪全都甩向后面,“让他学吧,埋死他!”
这回有了经验,在跨步时我们都不使劲踩进雪里了,并不把全身重量压在一只脚上,这样危险性太大。
通常都是一只脚刚落地,另一只也立即跟上落在同一地方,接下来的行程就安全了,大明在我们身后说,“我就跟着你俩踩过的走,那就没事对吧?”
事实也是这样,只不过,我不相信大林,橙子也不相信我,所以都是各自踩新的印子。
我们这边可以看到很远的其他雪山,它们沐浴在晨光里那么明净,巍峨耸立,白雪皑皑,连绵不断,冰雪将阳光反射到我们这边,使我们也感受了一下阳光的温暖。
这里是祁连山的龙脊,有点瘦削,地势偏陡,登山人一般不会选这里攀峰。
这里海拔大约在四千米左右,高度计不在我们这里所以只能粗略估计,空气质量比山下以及城市里要干净很多,吸进肺里一阵阵凉爽,格外的提神。
我们走了很长一段时间,大林说因为担心出意外,所以速度比以往慢了许多。
可是我和橙子都没觉得速度慢,我俩是紧跟慢赶的跟着队伍。
终于,大约在下午三点半左右,我们的行进的方向有了变化,突然开始向侧面弯转,地势逐渐变得平缓,前边人说快到目的地了。
我们提了提了精神,心想到了目的地肯定会休息一下。
我们是突然停止行进的,一时还没反应过来,前边的人就说已经到了。
我们转过一处山角,太阳暴露在我们的面前。
眼前是一大块的平地,看山体的影子,我知道这块平地的下面是个悬空的悬崖。
我告诉橙子我们在一块横在空中的山石上,这货来了一句,“二叔,你不会让我俩就在这下崖吧?”
二叔的目光越过众人落到我俩身上,“是啊,就在这下崖啊!”其他人开始笑,“他俩怎么才知道啊!”
这里还不是雪山的最顶端,至少离山顶还有个千八百米的海拔。
我战战兢兢的探出半个脑袋看看下面的情况,好家伙,立壁足足千仞高,完全看不到底,山壁表面平滑,根本没有好一点的落脚点。
就这么滑索下去,还不如让我直接跳下去更省劲,一了百了。
二叔在那边喊话了:“大家动手固定好绳索,四点左右就滑下去,我们只用手语不准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