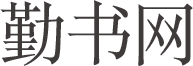第十章 一念之差
黄巢接到张归霸潼关失守的消息时,后者已在朱温的同州城内和弟弟张归厚大倒苦水了,不说自己玩忽职守的过错,只一味把蔡州兵马形容的无坚不摧。又说自己兵微将寡,哪里就抵挡得住虎狼一般的敌人?因此恳请弟弟代为向朱温求情,求这位同州防御使大人出头保住自己的一条性命。
张归厚如何会不答应自己亲哥哥的请求——待安顿好了张归霸并带回的残卒后,他急忙来见朱温。潼关失守非同小可,这意味着刚刚成立的大齐政权即刻就要面对兵临城下的险境。虽然一个刘剑锋并不可怕,但假如其它唐兵借道潼关,直扑长安,不出半个月,长安便会被围成铁桶一般,到那时,莫说是人,就是鸟也飞不出来了。
朱温正在与妻子张慧打赌,忽闻门子来报张归厚有要事相见,便来至前厅。待张归厚把潼关失守的消息告诉他,朱温惊得差点没从椅子上摔下来。
“大帅,还请您向圣上保下我哥哥的性命啊。”说着,张归厚“扑通”一声跪倒在地,“咚咚咚”地磕起头来。
朱温连忙起身相扶:“老张,你这是做什么?自家兄弟,哪里就到这个地步了?”
“大帅,还求您救救我哥哥。”张归厚跪在地上不肯起来:“我愿与我哥哥出兵夺回潼关,将功折罪。”
“你先起来,你哥哥我自然要保,只是如何保,我们还要想个万全之策。”朱温一边说着,一边想着还能找谁一起出面保张归霸。孟凯、盖洪这样的将领和自己原本就尿不到一个壶里,找他们只怕是与虎谋皮;虽然如今自己是整支义军部队中唯一一个统兵在外的将领,乍看之下外表光鲜无比,可是自己在义军队伍中根本没什么根基,如果不是潼关一战成名,那么他至今仍然只是一名普通的侍卫而已。以他的资历代张归霸向黄巢求情,恐怕后者根本不会卖他这个面子。张归霸的死活朱温从心底里讲根本不关心,但前日里和岳父一番交谈,深知在当今乱世,若想有一番成就,就必须有自己的势力——钱粮兵马倒在其次,人才是第一位的。张归厚是员猛将,朱温有心将他收归在自己帐下,此次若能救得他的兄弟张归霸,那么这二人日后必对自己忠心耿耿,如此也算自己有了班底,在义军队伍中,也不孤单了。想到这里,朱温抱定决心,不论这件事多难,他也一定要救下张归霸的性命。救下了他,就会让他的人望迅速升高,来日若谋大事,不愁无人襄举。打定主意的朱温把所有义军将领想了个遍,最后,他把所有的赌注压在了两个人身上——皮日休与葛从周。这二人从龙多年,对黄巢十分了解。而且,黄巢对二人亦是十分信任,如能说服此二人,则张归霸的性命或有可救。那么现在所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拿什么来说服此二人了。
黄巢接到张归霸潼关失守的消息时,怒不可遏得将报信之人直接推出去砍了脑袋——他想杀得是张归霸,可是这小子根本没来长安,率领残卒直奔同州了。可笑张归霸言之凿凿自己是到同州去搬救兵,誓要夺回潼关。这种话鬼都不信,同州还在长安以西,等他到了同州,只怕唐兵也就杀到长安城下了。
“拟旨——”黄巢说到:“着同州防御使朱温即可锁拿张归霸,就地斩首。”
“万岁——”翰林皮日休出班跪倒:“此事不可。”
“嗯?”黄巢一听有人出言相阻,便要发作,细看之下不是别人,乃是皮日休,不得不强忍了怒气,问到:“袭美有话要说?”
“万岁,那张归霸因何丢了潼关不来长安领罪反跑到同州去?”皮日休不答反问。
一语惊醒梦中人,黄巢猛然想起张归霸的弟弟张归厚此刻正在朱温帐下听令,张归霸不来长安,反奔同州,显然是投奔他弟弟张归厚去了。朱温作为自己刚刚提升上来的将领,根基不稳,而张归霸与张归厚俱是统兵多年的老将领,一旦闹僵事态,只怕朱温弹压不住,到时岂不是势成骑虎?黄巢想到这里,心内一片烦躁:“袭美,依你之见,又该如何?”
皮日休略一沉吟,回到:“万岁,张归霸投奔同州,朱将军对此事也应有所奏报,一动不如一静。依卑职所见,不如等朱将军的奏报上来,再做计较。”
黄巢思索一番,恍然大悟——倘使朱温对自己一片忠心,必然会将张归霸解来长安;而倘使朱温有什么私心,那么借张归霸此事,亦可以看得明白。
把张归霸放在一边,眼下头等大事便是备战潼关来敌,黄巢根本没将刘剑锋放在眼里,蔡州兵他也不是没打过交道,那不过是一群打家劫舍的兵匪而已,“和我比划?老子劫道杀人的时候你们还是老实巴交的庄稼人呢。”黄巢心想:“与蔡州兵交战,重在一个‘快’字,一定要趁来敌立足未稳之时给予迎头痛击,将他们赶出关外,不然一旦将仗打成胶着状态,等其它地方的唐兵赶来,那么大齐国只怕会比逃到巴蜀的大唐更先完蛋。”
“众将听令,吾等即可准备,兵发潼关!”霎时间,黄巢恢复了心情。他一点儿也不惧怕战争,相反,他对战争有着一种不可名状的向往——在他的眼里,这世道可杀的人太多了。他渴望战争,他渴望那种将冰凉的刀锋刺进敌人的胸膛时心底涌上的快意。
赵家村。
当日,陆旭遍寻不见玲珑与赵敬,又听与他同去的两名“黑云都”侍从回报说前面并无百姓活口,因此不顾那二人拦阻,来至街上一一翻查倒地的尸身,在遍寻数遍都没有发现玲珑与赵敬后,他心内暗暗欢喜,看来他们二人逃出生天,在兵匪洗劫村寨之前远远躲开了。而看到数日来与自己朝夕相处的赵家村百姓无辜受戮,心内又不禁生出无尽的悲凉。只是半天的功夫,原本鲜活的一个个生命转眼便成了一具具冰凉的尸体,他第一次对战争有了难以名状的厌恶感。他恨那些手执兵刃滥杀无辜的兵士,他更恨那些纵容手底兵卒劫掠百姓,涂炭生灵的将军统帅。此刻,在陆旭的心底,所有的仇恨都指向了一个人,这个人的名字,叫做黄巢。如果不是他起兵作乱,他的父亲就不会战死沙场;如果不是他放任属下,那么赵家村百十口乡亲的性命就不会白白枉送。
“黄巢匹夫,我恨不能寝尔皮,啖尔肉。当着赵家村死难乡亲的面对天发誓,我陆旭必与你为敌终身,到死方休。”
那两名“黑云都”的侍从几曾见过一个八、九岁的孩童立下如此决绝的重誓?因此不由得面色发觑,暗叫一声侥幸——若不是二人诳得陆旭在赵敬屋内盘桓数刻,让在村内砍杀的兄弟绕道撤出,那么屠戮赵家村的真相势必就会被陆旭撞破,到那时,只怕眼前这位小公子向刘将军告上一状,头里那些兄弟的脑袋立时就要搬家了。
“陆公子,此处极不安全,不如我们先回大营,等见过刘将军,我们再来为赵家村的父老乡亲处理后事?”
陆旭坚定地摇了摇头:“不,我哪里都不去。”说着,陆旭找来一把木锨,往赵家村后山走去。
“陆公子,你要做什么?”
“我要把他们都安葬好。”陆旭头也不回地答道。
两名侍从见状,心知很难再劝阻陆旭,商议一番后,他俩决定留下一人护佑陆旭,另一人回转刘剑锋那里去报信。
刘剑锋此刻心情大好。一战而定潼关,虽然事前有过这样的谋划,但是否能如期完成这一目标,心里却着实没底——潼关天险,绝非易与。当年六国合纵战强秦,秦国若非有函谷关这样易守难攻的关隘,只怕早已灰飞烟灭。而今日的潼关比当年函谷关的地势更险要,更难攻取。当年函谷关令六国无功而返,功败垂成——今日的潼关,更是令无数雄兵饮恨于此,徒留兴叹。谁曾想,短短数月内,潼关便被两度攻破,而其中一次,竟然是由自己完成的。一想到这里,刘剑锋就忍不住哈哈大笑,当他在副将的簇拥下登上潼关的城楼,不禁感叹到:“从今天开始,黄巢就要成为历史了。”
正意兴湍飞间,护送陆旭去往赵家村的侍从来至身前,凑在刘剑锋的耳边低语数句,然后站立一旁,等候刘剑锋示下。
刘剑锋听完那名侍从的回报,不禁眉头紧锁。众将不知缘故,纷纷交头接耳地猜测,是什么事情让主将如此为难。
过了一会,刘剑锋淡淡地对那名侍从说:“你去,率一个百人队到赵家村帮陆公子处理后事,跟陆公子说一声,本将因军务在身,不便即刻前往,稍晚我自会为赵家村死难乡亲主持公道。”
那名侍从面色一紧,抱拳领命而去。
“梁统领。”刘剑锋转身向一名副将说道:“你该约束一下你的部下了。”
那位梁姓统领不明所以,愕然道:“将军,何出此言?”
刘剑锋冷哼一声:“虽说是以战养战,也不用把一村的百姓都杀完吧?我问你,‘风’字营可归你辖制?”
梁统领一抱拳:“正是。”
“很好。”刘剑锋从牙缝间挤出这两个字:“诸位,我们到‘风’字营去转转如何?”
“风”字营内,从赵家村劫掠一番归来的众兵勇正相互炫耀着各人的战利品,虎皮、鹿角、三彩瓷器并金银首饰被争相展示出来。
“麻子哥,你手上拿的是什么玩意儿?”说话的人一把从一个满脸麻子的兵丁手里夺过来一根木棒模样的东西,只见这木棒长约四尺,木棒的一头被人从中间掏了一个凹槽,凹槽里又被楔进另外一根带钩的短木,在凹槽的四周,被人用铁片箍了两圈,显然是为了把那根短木更紧地嵌在那根长木中。“这锄头不是锄头、钉耙不是钉耙的,到底是干什么农活儿用的家伙什?”
麻子模样的兵丁“呸”了一声,从那人手中收回了那根木棒:“碾子,你就是个贱命,你也就认得锄头、钉耙。扁担倒了念啥你都不知道。”
众人一阵哄笑,有人问:“碾子,扁担倒了念啥呀?”
“念‘滚’,你给我滚一边去。”碾子被众人一阵笑,脸上有些挂不住:“你们都是富贵命,还不是跟老子一样,大兵头一个?”
众人又是一阵大笑。
“碾子兄弟,那个东西叫丸棒,捶丸用的。”人群中有见过的,高声叫道。
“去去去,我还不知道那玩儿意叫丸棒吗?我逗麻子哥玩儿那。”碾子故作早知道的样子:“麻子哥,是吧?”
“是个屁。”还没等麻子接口,被抢白的兵丁不依不饶地逼问着碾子:“碾子兄弟,既然你认得这东西,给咱们看看你的手段呗。”
这一下真难住碾子了,他才刚刚加入“黑云都”两个月,投军之前,他在蔡州就是个种地的农民,哪里知道捶丸是什么,更不用说给大家伙展示一下了。他面红耳赤地说:“我自然是有手段的,但偏巧今儿骑了一天的骡子,腰酸腿疼,没力气了。”
众人又是一阵大笑:“碾子,不会就不会,又说什么骑骡子没力气的话,哄谁呢?”
那麻子模样的兵丁也来凑趣儿,从怀里掏出一个鹅蛋大小的木瘤来,冲碾子摇了摇,说到:“碾子兄弟,你可识得这是什么?”
碾子凑近细看一番,只见这木瘤被人打磨得十分圆润,握在手中略有沉甸,心道这莫不就是那捶丸所说的丸球了?想到这里,他把腰一挺,不屑地说:“麻子哥,你也欺我不成?这自然是那捶丸所用的丸球了。”
麻子嘻嘻一笑,“碾子兄弟今儿既然乏了,我们也不难为你,这样吧,你只要说出这捶丸的输赢该如何计算,我们就服了你了。”
碾子想都不想,立刻说道:“这有何难,自然是谁将那丸球打得越远,谁就是赢家了。”
众人哄然大笑:“哈哈哈哈,碾子,大才啊。”
碾子一看众人又笑,心知自己露了怯,到底还是答错了,那原本就急红的脸此刻不由羞得更红了。他恨恨地把丸棒掷还给麻子,逞强说道:“怎么啦怎么啦?在我们那里,捶丸就是比谁把球打得远,你们有你们的玩法,不许我们有我们的玩法吗?”
众人一看这碾子还是个嘴硬的家伙,因此都有心要出出他的丑。于是有人说道:“即是这么着,咱们就依了碾子兄弟,麻子,这家伙什是你拿来的,你不妨就和碾子兄弟比划比划,看看谁把球打得远,谁赢了谁就得另外一人今天的战利品,大家伙说如何啊?”
众人一听,纷纷叫好。麻子一听也来了精神,拿眼一瞄碾子:“怎么样,兄弟,敢不敢啊?”
一句话就把碾子顶到了南墙上,他这会真是骑虎难下了。在“黑云都”的军中,但凡有这种打赌挂注的事儿,只要对方划出道道来挑战,你就得应下来,哪怕规矩再对你不利,你也得硬着头皮接招。不然,以后在军中便会成为笑柄,不但大家都瞧不起你,还会觉得这个人胆子小,日后上阵也是个怂包。在军中,如果谁不幸成为大家眼中的怂包,那他离死就不远了——没有人愿意和怂包在战场上并肩作战。
碾子一咬牙,把心一横,暗想,大不了就当这回什么都没得着。又暗暗看了一眼麻子,自忖胳膊腰身都比他粗些,拿个木棒把球打出去,想来也不是什么难事,自己也未必会输。因此不客气地回到:“有什么不敢的?你当我真赢不过你吗?”
众人于是“呼啦”一下散开,给碾子和麻子让出了一片地方。麻子当兵前本是市井间的泼皮,什么东西没见识过,这捶丸自是不在话下。前半晌随着大家到赵家村抢劫一番,不经意在一家人的屋内发现了四,五支丸棒和几个木瘤丸球,这一下子勾起了他当兵前的回忆,那时他和几个同伙就经常比试捶丸,赌些银钱。后来当了兵,一年中常有大半年的时间都在过提心吊胆的生活,总在担心不知道哪一仗下来,自己的命就没了,因此把从前那些乐子都忘记了,当他再看到这些从前的玩意儿时,忽然就让他想起没当兵时的惬意时光——因此顺手就把那一套丸棒一并取了回来,心想不打仗的时候,拿着这些玩意儿找找当年的感觉也是不错的。不曾想刚刚拿回来,就能用它再赢点东西。那碾子一看就是个土里刨食儿的货,别说捶丸了,只怕连丸棒怎么拿他都不会,这可是天上掉馅儿饼的买卖,刚刚碾子还献宝似的把他抢回来的两张虎皮大大咧咧的披在身上炫耀,他原本还懊恼自己为了这些丸棒白错失了发财的机会,没想到这土货竟愿意跟自己比捶丸,那虎皮可值不少银钱。一想到这里,麻子乐得嘴都合不拢了。
“我说碾子兄弟,咱可说好了,待会儿谁要事输了,谁可不能不认账啊,你那两张虎皮在哪儿呢,先拿过来。”
碾子瞪了麻子一眼:“谁输了不认账谁就是龟孙子。”
“好!”麻子心说要的就是你这句话,因此也不再多言,顺手从腰上拔出一把短刃,在一颗木瘤上刻了一道印记,然后把木瘤丢给碾子:“看好了,木瘤上有一道的是你的球,我的是没有的。”
碾子接了球,回到:“哪那么多废话,来吧。”
麻子一笑,将另一颗木瘤放在地上,回身从自己那一堆战利品中抽出一支跟碾子手中那根粗细相当的丸棒,对碾子说:“兄弟,我可没欺负你,你手中那根是朴棒,我这根可也是朴棒。”
碾子哪里知道捶丸的木棒还分着粗细大小,但听麻子这么说,也只得假装内行的回到:“我理会得。”
麻子眼滴溜溜一转,又说到:“碾子,既然咱们是按你们家的规矩来,那你就先击球吧。”
碾子一听,也不多言,把手中的木瘤扔到地上,只用右手握紧丸棒,把棒头对准那木瘤瞄了瞄准头,然后倒退几步,猛地向前冲过来,右手向后扬起丸棒,借着这一冲的劲道复又狠狠砸下来——孰料碾子这几步跑得有些猛,及至木瘤跟前的时候,他没能站住,整个身子都冲到了木瘤的前面,待那丸棒落下的时候,那棒头恰击在木瘤的底部,只听“砰”的一声,木瘤应声弹起,然后直接就冲着碾子的屁股飞去。碾子躲避不及,被木瘤结结实实的砸个正中,他“嗷”的一声叫唤,向前蹿出四五步远,然后丢了丸棒双手就去捂自己的屁股:“疼死我啦。”
碾子击球前那一系列的动作原本让众人看得目瞪口呆,谁都没见过一只手拿丸棒助跑击球的,还没等大家喝止他,不想碾子一棒砸下去,把个木瘤硬是砸在了自己的屁股上,那一棒的力道何其刚猛,众人倒吸一口凉气,暗想要是这一下打到自己的屁股上,还不得把屁股打开了花啊,因此都不由自主去摸自己的屁股,仿佛那一下真得就打在了每个人的屁股上一样,生疼生疼。紧接着,众人便笑得前仰后合,指着碾子的背影喊到:“好棒法——!”
那麻子亦是笑得连握棒的力气都没了,举在半空的丸棒不由自主地落下,从木瘤边擦着而过,那木瘤斜斜向前滚出一步左右的距离,就停了下来。众人一见,更是乐不可支。按照规矩,丸棒只要碰到了丸球就算是击打一次,碾子的木瘤虽然砸在了他自己的屁股上,但那木瘤却是停在了数步之外,原本稳操胜券的麻子却因为笑得太过忘形而乐极生悲,不小心落下的丸棒刚巧碰到了木瘤,却又没有吃准部位,因此这一棒下去,距离竟还不及碾子那失误的一击。麻子此刻追悔莫及,恼怒地把丸棒狠狠摔在地上,转身便要离去。众人一看纷纷喊到:“碾子,快回来,你赢啦。”
碾子在前面只顾龇牙咧嘴地揉自己的屁股,听身后众人这么呼喊,心内更是恼怒,只道众人有意诳他,拿他取乐,回身便要张口大骂,不防看见那麻子的木瘤竟真没有自己的滚的远,心内不由惊诧万分。再看麻子,一脸地哭丧模样被众人围住,分明是输了的样子。碾子不由转怒为喜,也顾不得疼痛,一瘸一拐地折身跑回来,嘴里嚷嚷着:“我赢了,我赢了。麻哥,说话要算话啊。”
众人正喧闹着,忽听得营门口一声唱喏:“刘将军到!”
陆旭在“黑云都”兵士的帮助下,将赵家村死难相亲的尸骸一一收拾掩埋。数月来的遭遇,一次次的生离死别,让这个年仅八岁的孩子渐渐开始觉醒。擦干眼角最后一滴泪,他做出了一个决定,他要去寻找玲珑与赵敬——他们是他在世上最后的亲人,他已经失去了太多,父母、家园;他不能再承受失去这两人所带来的伤痛。
趁着“黑云都”的兵卒不备,他悄悄躲了起来,等众人收拾停当时,才发现不见了陆旭,再去搜寻,哪里还能找到——众人无法,只得准备回营向刘剑锋复命。等兵卒们都走远了,陆旭从藏身之处出来,在村内被焚掠一番的各家又转了一遍,找寻了些换洗衣服和干粮,又来到众乡亲埋骨之地,重重磕了三个响头:“赵家村的爷爷奶奶,叔伯姨婶,陆旭就此别过了,我要去找玲珑姐姐和赵敬大哥了。等我找到他们,我一定会回来为你们报仇的。”
言毕,他站起身来,辨别了一下方向,心内思索道,刘将军的部队从东面来,假如玲珑姐姐他们往这个方向走,那么我在路上应该能与他们相遇,可见他们没有往东面去;逆贼的部队向西逃遁,二人自然也不会往那边去;北面有黄河,南面是山岭,赵大哥是猎户出身,自然是应该往南面而去。陆旭又想了一遍,觉得自己的分析没错,他暗自点点头,心说是了,自己只要一路向南,一定会遇见玲珑与赵敬的。
他哪里知道,赵敬与玲珑此刻早已渡过黄河,向东北幽州而去。这一念之差,致使姐弟二人从此天涯相隔,有生之年竟再没能见上一面。陆旭从潼关向南,入终南山有了一番意想不到的际遇,使他最终成为一代大侠;而赵敬与玲珑在幽州结为夫妻,婚后育有一子,取名赵弘殷,四十五年后,赵弘殷的儿子在洛阳出生,取名赵匡胤,960年,这个名叫赵匡胤的孩子在陈桥驿发动兵变,黄袍加身,建立了赫赫有名的大宋王朝,开创了中国的文治盛世。当然,这都是后话。
放下陆旭不说,且说刘剑锋来到“黑云都”的“风”字营时,恰遇上碾子和麻子二人赌斗捶丸,当他看到碾子那一棒将球击到自己屁股上时,刘剑锋也忍不住哈哈大笑。一时间差点忘了自己来“风”字营做什么了。直到守卫唱喏“刘将军到”,他才回过神来,于是板起面孔,不理众人,径自来至一座土坡处,对紧随在他身边的梁统领说道:“传令,全营集合。”
梁统领一招呼旗牌官:“快,传令下去,全营集合。”
旗牌官一抱拳,转身而去,不一会儿,“风”字营内响起闷雷般的号角声——兵卒们闻声纷纷披挂整齐,各执兵刃,来到空地前排列整齐。霎时间,整座原本喧闹无比的大营安静得不闻一声响动。
刘剑锋站在土坡高处,瞅着手底下这一营兵马,许久都没有说话,只用冰冷的目光在众人身上来回逡巡。梁统领不知手底下的人马何事惹恼了这位刘将军,却见他来了只命将人马集合完毕,又一言不发。心底不由琢磨,这刘将军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想到这,他干咳一声,来至刘剑锋身前:“刘将军,‘风’字营将士已经集合完毕,未知将军有何训示?”他哪里知道,刘剑锋心底此刻亦是处在左右两难的境地——“黑云都”之所以在战场上敢打敢拼,就是因为每个兵士都知道打赢了能抢夺战利品;而今天如果不将“风”字营劫掠赵家村的兵卒法办,心内又实在过不了那一道坎——陆恩庭对自己有救命之恩,自己的属下却将他儿子与义女所住的村庄劫掠一番,致使玲珑生死不明。究竟该怎么办?
梁统领试探性的问话打断了他的思绪,他下意识的挥了挥手,不想刚好做出了个解散队列的动作。下面的兵卒一看,更是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主帅今天这是怎么了?无端端把大家集合在一起,却又不发一言地让大家解散。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刘剑锋也是一愣,心说自己怎么做出了个解散队列的手势,不由更是一番意乱心烦,猛地大喝一声:“都给我站住。”
原本一边交头接耳一边准备回归营房的兵卒被这主将这么一喝,都吓了一跳,纷纷立定在当场,回头看着刘剑锋。
刘剑锋喝道:“今天前往赵家村劫掠的人,都给我站到前面来。”
兵卒们更是一愣,都怀疑自己是不是听错了?然后人群中开始窃窃私语,泛起一阵嗡嗡声:“怎么回事?赵家村是哪个地方?”
“不知道啊,是不是咱们今天去的那个村子。”
刘剑锋见无人应声,更是恼怒:“怎么,敢杀人放火,不敢承认吗?”
人群中,碾子傻乎乎地排众而出,来到坡地前面:“将军,我去了。”说着,他朝身后人群中一指:“麻兄也去了,还有牛三、刘田,还有……哎呦,你踢我做什么?”碾子回头,发现在自己身后站的不是别人,正是自己的什长:“哦,将军,还有什长,我们都去了的。”
是个人这会都知道刘将军是来找麻烦的了,大家正唯恐避之不及呢,没想到碾子竟不打自招了,不但如此,还把大家都供出来了。那些被碾子点了名的兵卒此刻恨不得上去直接把碾子那张嘴给撕碎了,因此一个个都目露凶光,咬牙切齿地瞪着碾子。
“怎么,还要我把你们一一都请出来吗?”刘剑锋在土坡上喝道:“都给我站出来。”
不多时,“风”字营半数以上的兵卒都极不情愿地来到坡地前面,人人噤若寒蝉,不敢出声。
“很好,很好。”刘剑锋缓缓走下土坡:“廷尉何在?”
“在。”
“未遵将领,私自外出,依法如何?”
“斩。”
“欺瞒主将,不听号令,依法如何?”
“斩。”
“滥杀百姓,劫掠乡亲,依法如何?”
“斩。”
廷尉三声喝斩,惊得这些兵卒们魂飞天外,“黑云都”自组建以来,从没有哪个主将在军中行使过这样的军令——虽然他们在入伍的时候,廷尉煞有介事地宣讲过“十三斩”的条例,但是这些年,“黑云都”的兵卒哪一个没有犯过这“十三斩”的条例?又有哪一个真得就因为犯了这些条例而被处斩?在“黑云都”的部队中,“行刑队”自成立以来就从未砍过自己人的脑袋。
刘剑锋喝道:“来人,把这些目无法纪、不听号令的都给我绑了。”
呼啦啦涌出一队兵士,将土坡前站着的兵卒们都绑了起来。
梁都统一看形势不对,连忙上得前来:“刘将军,这是何意?我‘风’字营的弟兄不知犯了什么错,竟要如此对待?”
刘剑锋一声冷笑:“怎么?我堂堂先锋官要做什么,还要向你一个小小的都统交代不成?”
“不,末将不是这个意思。只是——”
“只是什么?给我噤声,一旁站下,待会再算你的帐。”说着,刘剑锋转身冲下面喝道:“还愣着做什么,都给我推出去,待陆公子回转大营,斩首示众。”
“将军饶命。”
“将军饶命。”
下站的兵卒一听要砍头,纷纷大声乞嚷:“将军,我等身犯何罪?要将我们处斩?”
“是啊,我等身犯何罪?便要处斩?”
刘剑锋横眉怒目:“好胆,还要问身犯何罪?尔等在赵家村烧杀劫掠,打量我不知道吗?”
众人一听更是不服:“将军,咱们军中,哪个没有烧杀劫掠过?为何只因一个赵家村,便要砍我们的脑袋?”
刘剑锋焉能不知军中兵士都有过烧杀掠夺的行径?但他如何能跟这些人说,只因为你们误劫了我救命恩人儿女所住的村庄,我就要拿你们的脑袋抵命?
他冷冷地说道:“杀你们自有杀你们的道理,尔等安心上路,家中老幼,本将军自会善加体恤。”
说着,再不理众人的求情声,就要命行刑队将一干人拉出行辕,准备处决。
正在这时,行辕外一骑飞奔而入,直驱至刘剑锋身前:“报——刘将军,陆旭陆公子不见了。”
“什么?”刘剑锋听得奏报,惊诧不已:“如何就不见了?”
来人将情况一一回明,刘剑锋听完奏报,心中暗想,莫不是走漏了风声,那陆旭得知在赵家村行凶的不是别人,正是自己的属下?自己原本是要将这些士卒就地处决,给陆旭一个交代,如今走了冤主,倘使此刻便将这些人杀了,日后寻见陆旭,只说已将犯事的兵卒处斩,恐难令他相信。想到这里,他说道:“且慢行刑,将这些人各打二十军棍,先行收押,待寻见陆公子,再行处斩。”说着,他又命部将多派人手,四下寻找陆旭,心内不由感叹,陆将军,刘剑锋对不起你啊。
葛从周下得朝来,就听门人奏报,说同州有人来见。在朝上,葛从周得知张归霸丢了潼关,不到长安领罪,反投朱温。因此,他现在多半已猜出来人的身份及想要做什么。略一思索,葛从周命门人将同州来人带至花厅,他十分感兴趣朱温要对自己说些什么。
不多时,同州来人被带至葛从周的面前,葛从周细细打量了来着,不由觉得有些诧异。此人长得十分单薄,且眉目清秀,不着军装,倒是一副秀才的打扮。
“你是何人?”
“小人敬翔,现在朱温朱将军手下听差。”
“哦,你家将军着你前来,有何事情?”
敬翔微微一笑:“葛将军性命危在旦夕,我家将军着我前来搭救于您。”
那年秋天走到最后的光景时,鱼玄机也迎来了她生命最后的时刻。临刑前一天,鱼玄机忽然恳请张直方为她弄来一副丸棒:“记得我嫁给李郎时,他最爱捶丸了。每日里我们除了吟诗作赋,最美的时光就是一同下场比试捶丸。我曾特意写过一首诗,怀念那段日子,张大人,你可要听?”
张直方点点头。
“坚圆净滑一星流,月杖争敲未拟休。
无滞碍时从拨弄,有遮栏处任钩留。
不辞宛转长随手,却恐相将不到头。
毕竟入门应始了,愿君争取最前筹。”
鱼玄机边吟旧作,边用丸棒轻轻把丸球从牢房内通过栅栏的缝隙推到牢房之外。“张大人,你说明天,李郎会来送我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