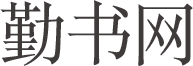正在阅读> 一代钱王> 章节目录> 第一章 钱王出世---险遭亲爹丢弃
第一章 钱王出世---险遭亲爹丢弃
烟花三月,花红柳绿春意盎然的大好时节。
是夜,钱宽待产的娘子睡得正熟,突然被钱宽杀猪般的嘶吼声从睡梦中惊醒。
“妖孽,你休想来祸害我们家,有本事你出来,赶紧给我滚出来!”双眼紧闭的钱宽一边说着,一边挥舞着双手,看那架势,像是在跟什么人决一死战。
“官人,又做噩梦了吗?快醒醒!官人!”水丘氏扶着床沿挺着大肚子笨拙地坐起来,轻声将钱宽摇醒。
被唤醒的钱宽睁开眼睛后发觉原来是在做梦,便如释重负一般长长地舒了一口气,然后,接过水丘氏递过来的毛巾胡乱抹了一把额头的汗。
水丘氏温柔地问:“你呀,这几天夜里总是喊打喊杀的,仿佛跟魔鬼附了身一样怪吓人的,是不是梦到什么可怕的东西了?”
钱镠若有所思地回头看了水丘氏一眼,他很想告诉妻子梦中那不可描述的可怕情景,却又怕妻子担心影响到肚子里的胎儿,因而几次欲言又止,他看了看水丘氏那如同扣了个箩筐一般高高凸起的大肚子,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没事儿,胡编乱造的一个噩梦而已,没什么可怕不可怕的!”
水丘氏见他不肯说,便也不再过问,一阵困意袭来,她打了个哈欠吹灭了蜡烛,躺下继续睡。
钱宽是杭州临安大官山钱坞垅村的村民,近日来,他接二连三地做着同一个噩梦,几乎每晚都会把要待产的妻子水丘氏吵醒。
这一次被妻子摇醒后,钱宽便再也没有睡着,心中一直在反反复复地琢磨那个奇怪又可怕的梦。等到天一亮,便心事重重地出了门,把临产的妻子扔在家里,独自去邻村的一位好友家饮酒叙话。
这钱宽出生于耕读世家,他的祖父曾经任安徽旌德县令,告老辞官后携带家眷归隐此地。钱宽平日以种地打渔为业,闲暇时喜欢与好友吟诗作对,日子过得优哉游哉。
现如今,钱宽也算是有家有业有妻有子,虽然孩子还没生出来,但估摸着也就这几天的光景了。
按说,妻子大着肚子这个时候他不该外出,但是,接连几天做着同样的噩梦却让他心里惴惴不安,总担心未出生的孩子会有什么闪失,或者家里发生什么灾祸。说出来怕影响妻子的心情,憋着不说他又心里郁闷得慌,只好来找好友喝喝小酒解解闷儿。
与好友年龄相当,意气相投,钱宽一来老友便摆下酒菜好生招待着,钱宽也不客气,一屁股坐下来两人直接就喝上了。
“你这几天的情绪不太对啊?怎么看上去心神不宁的?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好友放下筷子,盯着钱宽问。
“哎别提了,我昨夜梦到一个火妖要来烧毁我家,心急之下我操起桃木剑照准妖怪的头砍过去,结果你猜怎么着?”钱宽故作神秘地问道。
“怎么着?脑袋砍掉了又长出来一颗?”好友没个正经地取笑道。
“那妖怪化作一缕耀眼的火光钻进了我娘子的肚子里去了!哎!我真担心那妖怪会祸害了娘子肚子里的孩子啊!”钱宽叹了口气,夹起一粒花生米塞进嘴里旁若无人般嘎嘣嘎嘣地咀嚼着。
“一个梦而已,瞧瞧把你吓成啥样了?人哪有不做噩梦的?你呀,就别成天为这点儿没谱子的事儿瞎琢磨了,放心吧,咱娃福大命大不会有事的!来来来,喝酒喝酒!”好友说完,便抓起酒瓶子给他添酒。
“哎,话是这么说,可是以往我做的梦从来没这么真切,也没让我这么提心吊胆过,我总觉得这个梦不是个好征兆啊!”
钱宽叹了口气,端起酒杯正砸吧地津津有味儿,这时,钱宽的一位邻居呼哧呼哧地跑进来,上气不接下气地说:“宽哥,快别喝了!呼呼~你家娘子要生了!赶紧回家悄悄去吧!”
“娘子要生了!娘子要生了!”钱宽喃喃自语地重复着,急得连招呼都没跟好友打,扔下酒杯拔腿就往家里跑。
好友家距离钱宽所在的村子不远,约莫也就五六里地,等钱宽和邻居大哥气喘吁吁地跑到村里的那条小路时,远远地看到自己家的房屋周围被一片通红通红的火光笼罩着,伴随着红光的还有一片令人胆战心惊的兵马声。
“宽,宽哥,你家房子,好像着火了!”邻居指着钱宽家的房子气喘吁吁地说。
没等钱宽反应过来,邻居接着说:“我好像还听到了兵马声,莫非是谁家犯了重罪朝廷派来人抄家了吗?哎也不对,咱们村好像也没有在朝廷做官的啊!”
“完了完了!噩梦应验了!造孽啊!”钱宽双眼直勾勾地盯着那一片火光心一点一点往下沉,想不到,那个梦真的应验了,他担心的事情这么快就发生了。看来那火妖是真的要把他烧干净啊!想到这儿,钱宽使出浑身解数一口气冲回了家。
“娘!娘!娘子!娘子!你们别怕!我来救你们啦!”钱宽推开院门大呼小叫地冲进去,屋内传来一声如同野兽嘶吼一般的啼哭声,吓得钱宽忍不住打了一个激灵。
“哎哟我滴儿啊!你总算是回来了!救什么救啊?是不魔怔了?你可小点声别咋咋呼呼的吓着我大孙子!瞧瞧这都当爹的人了,怎么还这么毛毛躁躁的?”钱母说着,甩着膀子用力地拍了下钱宽的胳膊。
虽然钱母嘴上嗔怪着,可脸上的喜悦却掩饰不住地往外溢。
“娘,咱家没着火啊?我娘子她怎么样?孩子还好吗?没缺胳膊少腿或者……被毁容什么的吧?”钱宽一口气把心里担心的全部掏出来后,便推开房门火急火燎地往里走。
“啊呸呸呸!这大喜的日子你在这儿胡咧咧什么呢,”钱母赶紧双手合十十分虔诚地祷告着,“老天爷呀,您可千万不要怪罪呐,我儿他年纪小,第一次当爹八成是高兴坏了,莫怪莫怪哟!”
钱宽看母亲十分欢喜的样子不像是有什么事儿,心里的一块石头总算落了地。
“那大娘,哥,既然是虚惊一场,那我就先回去了,家里等着吃饭呢!”邻居说。
见钱宽没做声,钱母赶紧迈着小脚挪着小碎步跟出来相送:“有劳大侄子跟着跑腿操心了,等孩子满月了过来喝酒啊!”
“好嘞!”邻居说完,迅速闪离了这是非之地。
钱宽推开门,看到娘子因为过度劳累已经昏睡,钱母迈着细碎的步子走过去,将孩子抱在怀里,满面春风地笑着递给钱宽:“儿啊,别傻愣着了,快来看看你儿子!瞧,长得多威风!长大以后一定是个武将。”
钱宽把手伸过来,撩开包裹的小被子低头去看时顿时被吓了一跳,只见这孩子长得那叫一个不堪入目啊!黑皮肤,四方口,倒八字眉,面目狰狞其丑无比,一副凶神恶煞的模样,不哭不闹,一双小眼睛紧闭着,一点儿孩子该有的可爱劲儿都没有。
钱宽看着看着皱起了眉头,这样子太熟悉了,跟他昨夜梦里梦到的那个丑陋的火妖相差无几,看看这满室经久不散的红光,再回想起那妖怪钻进娘子肚子里的情形,钱宽顿时毛骨悚然。
这哪儿是生了个孩子呀,这分明就是生了个妖孽,生了个祸害!这隐约的兵马声就是个凶兆,仿佛在暗示他,如果他此时不除掉这祸害,恐怕将来真的会被这妖孽霍霍的满门抄斩家破人亡!
想到这儿,钱宽忍不住打了一个冷颤,二话不说揣起孩子闷头就往屋后走。
“儿啊,你这是要抱着孩子去哪儿啊?你可仔细着点儿,千万别闪着腰抻着胳膊腿什么的!等明天一早啊,你就去你老丈人家报喜,鸡蛋娘都给你准备好了,一会儿啊,我就去把它们染成通红通红的,喜庆!”钱母喜滋滋地跟上来说。
钱母不知道儿子昨夜的那个噩梦,自然也就不知道他心里的恐惧,更不知道他此时此刻心里在琢磨些什么,还以为是钱宽刚做了父亲心里头高兴,要准备抱出去给街坊邻居们瞧瞧,分享一下喜悦的小心情。
“娘,别瞎忙活了!这个孩子不能留!”闷了半天没说话的钱宽语出惊人,把钱母着实吓得不轻,那孩子仿佛知道自己马上就要死翘翘了,本来安安静静的他,此时仿佛在为自己喊冤似的,扯着喉咙皱着鼻子咧着嘴吧撕心裂肺地哇啦哇啦哭个没完没了。
“你说什么?”钱母脸上的笑容顿时凝固了,她不敢相信地看着自己的儿子。
“娘,别人家的孩子要么随爹要么随娘,你仔细瞅瞅他长得,既不随爹也不随娘,我看八成是随了鬼了!”钱镠没好气地发泄着。
“啊呸呸呸!什么鬼不鬼的不要胡说八道!你难道没听说过丑人有丑福吗?细皮嫩肉是能当饭吃还是能当柴火烧?一个男娃,又不是去当戏子!长那么好看干啥?我大孙子将来可是要靠本事做大官的,不是靠脸蛋儿吃软饭的!”
钱母像所有祖母一样护犊子,她觉得,这娃丑是丑了点,但是再丑也是他们钱家的命根子,既然是钱家的根儿,就得好好疼。
“娘,我不是嫌他长得丑,我是怀疑这孩子是个妖孽,如果今天不除掉他,恐怕将来会给我们家带来意想不到的灾祸啊!”钱宽说着,加快了脚步跨出门槛儿,迅速走到屋后的那口水井旁。
俗话说水火不容,这妖孽不是火妖吗?那就只能扔进水里才能镇住他,然后结结实实地将井口封住,如此一来,就算这孩子是恶鬼投胎,想来也兴不了风浪作不了啥妖。
手刚要举起时,原本晴朗的夜空突然划过一道闪电,随后响起一声巨雷,紧接着下起了倾盆大雨。
“儿子,虎毒不食子啊,你有什么证据证明这孩子是妖孽啊?你年纪轻轻的怎么能这么糊涂呢?”钱母闻言后,两只小脚如同上了发条一样飞快地冲过去,一把将孩子夺过来护在怀里。大雨如同瓢泼一般哗啦哗啦地下着,站在暴雨中,钱母多病的身子显得格外单薄。
钱宽见母亲阻拦,便原原本本地将自己近几日夜里重复做着同一个噩梦的事儿说给母亲听,原本以为母亲听完后能够认识到事情的严重性同意自己的决定,想不到钱母不但没有半点儿恐惧,反而更加坚信这孩子就是天神下凡,将来一定会有大作为。
“这孩子既然三番两次地托梦给你,那证明咱们家的日子从此就要红火了,这是火云神下凡,你可万万不能动他! 娘今天就把话撂这儿,这孩子就是娘的命根子,如果他有个三长两短,我老太婆也不活了!”钱母见儿子执迷不悟,只能以命相胁。
钱宽是孝子,见不得母亲生气上火,既然母亲执意要留下这孩子,他也不敢忤逆。而且母亲说的似乎也有道理,具体是妖是神他也分不清,反正现在看起来好像也没啥事儿,所以,他决定遵从母亲的意思,把孩子留下,并取名婆留,意思便是阿婆留下了他。
然而,也就在那天起,钱母就患上了寒疾,天一冷就止不住地咳嗽,此后,就三天两头的抓药。怎奈家中不太宽裕,没有多少余钱请更好的大夫抓更好的药,因此,钱母的病一直都未除根。
虽然留下了这孩子,但钱宽对于这天生异象的孩子还是不太放心,为了让他本分一点少惹事端,小钱镠在七岁的时候就父亲送到私塾研习诗文,并将他的名字改为钱镠,希望他能像纯金一样,经受得住烈火的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