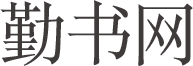正在阅读> 大明神探张梦鲤5大理寺卿> 章节目录> 第九章:师邵墨坊问马瞻
第九章:师邵墨坊问马瞻
话分两头。此时十余里外的“阳井村”,马备正装作一副仁善模样,敲响了韩启廉家的院门。
过了好些时候,才闻韩玉枝在院里隔着门问道:“谁?”
马备见韩玉枝有些警惕,立马脑瓜一转,回道:“我是受人之托来要钱的。这是韩启廉韩官人的家吗?”
韩玉枝听他说要钱,虽然还不肯开门,但却因好奇放松了些警惕,只听她又问对方道:“我是韩启廉他妹妹。我家何时欠过你钱。”
马备又道:“姑娘误会了,是这么回事:我是大街上买糖果的。昨天晚上有个自称叫韩启廉的年轻人见我面善,跟我说他茄袋不见了,因为有事暂时回不了家,想从我手里借几两银子暂渡难关。我虽然心好,但也不敢贸然拿辛苦挣的钱去冒险,后来他拗不过我,我也不忍心拒他,就只答应帮他来问家里人要钱。这不,我问了他家里住址就赶来了。姑娘要还不信可以先找官府的人做个见证,我要是骗你随时把我抓去蹲大狱都行。我就是个帮忙的,你要信就开个门,要不信我就走了。”
韩玉枝听他说得有板有眼,真以为是哥哥在城里丢了钱袋找人帮忙,一时心急也没考虑太多,仅存的那点警惕心也早抛之脑后了。开门见了马备,对方十分客气地抱拳行了个见面礼。左一个姑娘,右一个官人的,十分礼貌。听他言谈举止倒也不像坏人,偶然挪动脚步时韩玉枝见他还是个跛子,自然更是放心不少。
只因晓得他腿脚不便,又矮又瘦,谅也不敢做什么出格事体。所以韩玉枝也没再多想,真当个好人一般将他迎进客堂。
一入座坐定,韩玉枝真以为他从京城赶来帮忙,路上受了冻饿,赶紧先倒了杯现成的热汤给他暖手,又泡了壶好茶给他招呼着。
好一阵子,马备嘴里不再喘白气了,便客气道:“姑娘真是好心,看来韩官人真是遇上难处了,没骗我。早知道我就答应借他银两了,还不至于跑这么一趟。”
韩玉枝急于打听哥哥情况,忙问道:“大叔,我哥哥让你来时有说他现在住哪儿吗?”
马备本是来套她话的,哪里知道这些,不过韩玉枝这么一问,倒使他找着了机会,他先摇摇头,瘪嘴道:“这个他没说,我问他时,他只说你知道那地方,让我问你便可。”
“我哪知道?”韩玉枝也是心急失言,脱口便说道,“昨天他只说会在京城找个客栈落脚,也没定具体是哪家客栈,问我我也说不上来。”
“这就麻烦了,我看官人他当时脸色也不是很好,心情亦不佳。可是遇到什么事了,以致不能回家来?”
韩玉枝刚想要回,又觉得和外人说太多总是不好,便打个幌子敷衍过去。马备也识趣,并不多问,只叫她取十两银子给韩启廉带去。韩玉枝担心哥哥,也顾不得银两会不会被骗,依数给了马备,还另拿出两钱用作谢银。
马备取了银两,立马回了衙门,此时张公和范右堂已不再县衙,只有在后堂等候消息的吴允江。
马备到了后堂,吴允江见其回来,忙起身把后堂大门一关,小声问道:“本官交代你的事办得怎么样了?”
“卑职已经打听清楚了……”马备凑到吴允江耳边,将阳井村一行详细陈来。
待吴允江听罢,很是满意,同时也有些疑惑,问马备道:“你是如何知道韩玉枝会上你的套的?万一她什么都不肯说,甚至怀疑你,那岂不是会打草惊蛇?——现在想想你也是冒了个大险,下不为例啊!”
马备咧嘴一笑,颇有些自负道:“大人多虑了。从卑职在韩家捡到的那封信来看,韩启廉对首辅大人大力推广新法一事颇有微词,而且这信是写给他的老师——也就是当朝的刑部尚书严大人的。如此机密的信其中意味着什么韩启廉比谁都清楚。他也许还不知道信在谁手里,但信平白无故不见了就已经够他发愁的了,再加上刚刚和他有过关于新法争论的卫该被杀了,不管他是不是凶手,他都有必要出门避避风头。那个姓邓的村长看样子一心想着沾他新科进士的光,所以他知道卫该的事后一定会第一时间告诉他并从中相劝,韩曾受过村长的恩,自然不会不听。所以,当我从这方面着手用模棱两可的话试探韩玉枝时她根本不知道我是在探她口风。我说我是大街上卖糖果的,但并未说是京城的大街,只因她知道韩启廉在京城,所以自然而然地以为我说的就是京城大街。我说韩启廉因为丢了钱袋托我帮忙带钱,由于韩在外避风头,出现这种情况是十分正常的事。再加上我特意说了一句他是因为有事回不去才托人帮忙回家取银两的。韩玉枝听我这么一说,自然以为我说的都是实话——如此一来,要套出韩启廉身在何处又有何难呢?”
“妙哉!”听了马备这番分析,吴允江忍不住赞道,“让你只做个县丞倒似还有些屈才。”
“大人过奖,”见大人夸奖,马备连忙谦虚道,“愿一直随大人鞍前马后,誓死效劳。”
“只是有一点比较麻烦,”吴允江突然又眉头一皱,提出新的问题,“我们只知道韩启廉在京城某家客栈,但偌大个京城这么多家客栈,如何能轻易找得到他?”
马备狡黠一笑:“整个京城我们要找人确实不易,但再难还能难住锦衣卫吗?”
“噢……”吴允江恍然大悟,两人四目相对,心照不宣地大笑起来。
笑罢,吴允江又一脸严肃道:“这一条鞭法是我恩公的毕生事业,决不能出半点差池,况且事关社稷。本官无论是于忠还是于义都应该支持首辅大人。韩启廉公然反法,和支持新法的卫该闹了矛盾,这件事必须严查到底。如果真是他一时激愤杀了卫该,那就是罪上加罪。不管是谁说情,本官也绝不姑息!”
马备是个聪明人,自然明白上司心里在想什么,遂点头应承道:“大人忠义两全,乃我辈之楷模。大人请放心,卑职知道该怎么做了。”
酉时许。在良乡县以西十三里,一辆马车在一间作坊门前停住,随后便见身着常服的张公和范右堂从马车上下来。
范右堂付了车钱打发车夫自去,之后转身和张公一起看向坊门上的招牌,牌上有四个雕漆大字——师邵墨坊。
“应该就是这里了。”范右堂道。
张公点头,准备登门入坊。只是还未及跨上门前台阶,就从旁边墙角转过一个年轻人,把两人拦下:“这是作业重地,不是工人不让进,你们是做什么的?”
范右堂在旁道:“我们不进也行,我家大人要找你们马老板。”
那年轻人见两位身着华服,腰挂美玉,不像等闲人物,也不敢贸然拒绝,只是道了句“且稍等片刻”便进门通报老板去了。
不消多时,马瞻便展着笑脸走了出来。他本以为是吴知县找上门来问话,不曾想却是两个生面孔,便狐疑道:“两位是?”
张公看了眼半掩的坊门——里面正传来工人的吆喝和生产作业的声响,于是道:“马老板,这里太嘈杂,借一步说话。本官有话要问你。”
一听“本官”二字,马瞻刚刚消散的笑容又急急忙忙挤回那张脸上。笑着跟张公二人到了一稍微安静点的地方后,方才问道:“既然两位是官府公干人员,想必还是为了我卫兄弟的案子吧。”
“没错,”张公开门见山道,“我要你把死者那天和人争吵的事再详细讲讲。”
马瞻道:“这事我已经告诉过良乡知县吴大人,两位大人何不找他一问?”
“不,本官现在接手卫该一案,所有关于此案的消息必须保证是第一手来源。”
范右堂在旁故意做出不耐烦的样子,呵斥道:“让你说你就说!问什么问题那是大人的事,你只管如实回答就是。”
“大人莫恼,我说便是了。”见对方生气,马瞻也不想在这节骨眼多事,便将那日之事从头说道起来,“本月初四那天早上……”
因马瞻此番说与张公的与那日在公堂所说并无二致,故此处不再复述。只道马瞻说完后,张公面露疑色,问他道:“你说韩启廉和卫该发生龃龉后,有报复杀人之嫌,未免太过勉强?”
“大人那是没在现场看到,”马备道,“我要不拉他俩估计当时就得打死一个。不过,要真是这样,恐怕死的就是姓韩的了。”
“何以这么说?”
“大人您想想看,那韩启廉也就是脾气大而已,要真斗起来他一文弱书生怎么打得过常年劳作的卫兄弟。但如果是他恶意报复半夜搞偷袭那就另当别论了。”
“这么说,你也认为那晚的穿窬之盗就是一心想要报复的韩启廉了?”
“大人,这话我不敢说满,但从两人争吵、卫家失窃到卫兄弟被杀三件事的时间关系上看,这种可能没有十成也有八九。”
张公此时陷入了沉思,良久没有开口。马备等到最后忍不住问道:“不知二位大人还想打听什么?若没别的事我就先回去了,实不相瞒,墨坊还有一大堆事等着我去忙呢。”
张公这回才摆摆手,任他去了。范右堂对张公道:“大人,天色不早了,我们是回县衙还是直接回大理寺?”
张公缓缓道:“不,哪里都不去,找家客栈住宿便可。”
到了戌时,二人已在城中一家名为“如梦令”的客栈下榻。张公先叫店家拿了酒菜吃过,之后两人隔案对坐,就着一豆之灯夜谈起来。
“右堂,”张公道,“卫该一案你有没有发现什么不对劲的地方?”
“大人是指死者还是凶手?”范右堂反问。
“我是指窃案和命案之间的联系。”张公道。
“莫非大人也相信凶手就是那贼了?”
“不全是。正如你之前分析的那样,如果真是以窃财为目的的贼,他不会在院里有人有灯的情况下去冒险行动,况且就像你说的,第二天就是卫该新赚取货款的日子,他没理由不等到钱更多的时候再动手。所以,本官可以百分百相信的是当晚闯进卫家的人目的不在盗窃,而是另有目的。但其真正的目的却不一定是杀人。”
“如果是在达成其他目的的途中被卫该发现并制止,之后失手将他杀害呢?”
“这倒有可能,但可能性不大。”
“大人的依据是……”
“你仔细想想看。李美姑曾说过,当晚她穿好衣服后出门就没看见丈夫和贼。如果他们是当时扭打在一起,那么李美姑不可能不知道,就算两人追逐到院外,其他邻居也不可能一个都不知情。所以这种失手杀人的说法也很难成立。”
“那照大人的意思只剩下一种可能了——入室盗窃者其最终目的并非为财,而是别有目的。而杀人者亦另有其人。”
“唉!”张公叹了口气,“照目前我们掌握的线索来看确实如此。不过本官现在还在考虑马瞻说的话。”
“大人是认为他撒了谎。”
张公摆手:“那倒不是,正好相反。他和韩启廉无怨无仇,没理由说假话陷害他。”
“那听大人的言外之意,是韩启廉……”范右堂说到此故意停住,并用探询的目光看着张公。
张公想了良久,最终颇感无奈道:“但愿非我所想吧。若韩启廉果真有违国法,那我也只能得罪公直兄了。”
“大人无消多虑,”范右堂慰藉道,“若姓韩的果真做了什么伤天害理的事,那他就是有负师恩,届时严公定会与他断绝师生情谊无疑。况严公为官清正无私,人如其名,若姓韩的真有这等恶行他自然是支持大人秉公处理的。”
“说的是啊!”经范右堂这么一说,张公心下释然,并道,“不过这些也都是我们的猜测罢了。明日一早,我们分头行动,我再去一趟卫家,先解决窃贼是否就是凶手的问题。你回县衙,盯紧吴知县。这次韩启廉公然反法,张居正不可能不管,如今他儿子已经派锦衣卫介入此事,我们要小心应付才是。本官不管什么大局小局,新法旧法。只要我在大理寺任职一天,就不能放任无辜者受冤,歹恶者逍遥。”
“下官领命!”范右堂听得热血沸腾,义愤填膺地回了一句。
此时张公见夜已更深,便吩咐熄了灯,各自回房歇息,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