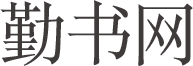正在阅读> 桃源梦> 章节目录> 第三十章 峰回路转……
第三十章 峰回路转……
峰回路转 返璞归真如历梦
柳暗花明 农民似牛出困井
为了使学习班问题能得到真正的解决,1975年2月12日,农历乙卯年正月初二,吃过早饭以后,东圩村学习班里的人,趁着过年,邀约着赵荣雨,要一同去找洪笑峰讨说法。赵荣雨知道,事情到了这种地步,洪笑峰本人肯定是没有明确答复了。于是说道:“这件事已经把我弄得昏头晕脑,我也抱定了无所谓态度,不想去呢。”于是,他们相约了九个人,来到公社所在地——新镇街上洪笑峰的家里。
洪笑峰正在自己卧室里看红宝书。他在百姓面前高高在上已经习惯了,哪还把东圩村这班小青年放在眼里。见他们来了,毫不理会。这班小青年见状,不问三七二十一,七张八嘴地质问道:东圩村学习班的问题,已经这许多年了,为什么还不给结论?我们要真是特务,你怎么还不把我们抓起来?不是特务,为什么还不给我们一个说法?老是这么不明不白的摆着干什么?我们都是青年人,难道就要被这件事蛮缠一辈子么?你也是为人之父,你家孩子要是遇到了这种情况,你心里是怎么想法?
洪笑峰见这许多人一副声讨的样子,脸色变成了猪肝色,不得不理会了。他从卧室里走了出来,干咳了两声,强装镇定,满脸堆笑,假惺惺地说道:“你们都是东圩村的?啊,怎么没在家过年,到这里来了?”
董正玉的儿子董尚彬,颇有乃父之风,说道:“洪书记,只有你才能过好年呢!我们平白无辜地被人诬陷为特务,都这么多年了,还有什么心情过年?能过什么年啊?”
洪笑峰嘴巴裂了裂,说道:“哎呀,小同志,你怎么能这么说呢?大家都一样,为什么就我才能过好年呢?”
董尚彬说:“不是吗?说我们学习班是特务组织,都这些年了,是与不是,也不做结论。把我们政治上搞得不明不白,我们哪有过年的心思?我们到底是不是特务,请你现在就给一个说法!”
洪笑峰脸色变成了霜打的茄子,紫得发黑。虎着脸说:“这是过年!你们想借这个机会无理取闹吗?谁说了你们学习班是特务组织?现在人保组在那里,你们有话去找他们说去嘛,在我这里胡闹什么?”
董尚彬见他打着官腔,想推卸责任,加重了语气说:“是谁在胡闹呀?无故陷害我们的人才是胡闹呢!我们好好的,你不知道在哪里听到了什么风和雨,就跑到东圩村上硬说我们是特务;闹得我们不人不鬼,现在又不管不问,却在家里安心过你的快活年。我们已经被陷害着这么许多年了,你还打算把我们陷害到哪一天?我们到底是不是特务,你今天一定要给一个说法!”
这里许多人闹哄哄地,早有人报告了公社常委、曾经与洪笑峰一同来东圩开会,说东圩有特务的章家帆。章家帆自恃与东圩人熟悉,快步赶来说:“哎呀,大过年的,你们怎么跑到这里来了?快回去,快回去。这个事情嘛,人保组会给你们解决的。和洪书记讲,洪书记也不能答复你们。这事我负责,等人保组过了年再来,我就向他们反映。你们放心,你们放心!” 章家帆认得几个人,又个别地拉着到一旁好说歹说。
这九个人也是为了有个台阶下,终于被“劝”了回来。他们回到村上后,精神为之大振,都说,这些当干部的,你怕他们,他就欺负你。章家帆说会给我们答复,到时候如果还不给答复的话,我们再找他去!
1974年3月22日,农历二月二十九的上午,人保组秘书长、驻韩庄大队负责人赵成和,在东风生产队劳动的田头——墩塘的大路旁,特别召开社员大会。他直截了当地宣布:“东风领导组在原来领导组干部不变动的情况下,增加赵荣雨同志为领导组成员、任政治队长。”生产队从来没有政治队长的职务,于是,他解释说,政治队长是什么职务呢?好比是大队的书记,是第一把手。可以代理生产队队长的职权,团结生产队干部和社员把生产搞好。原来在赵荣雨办的学习班里的人,都解除嫌疑,与普通革命群众一样,能入党的入党,能入团的入团,能当兵的当兵。他们在政治上的进步,不受任何影响!
在场的人听了,不顾身在田边,许多人跳了起来,还有许多人欢呼起来:五年了,这些无辜的孩子,到这时候才算得到了公平!真是折磨得他们太久了,太久了!
赵成和听了,在心里说:“是太久了啊!可是,如果不是我们人保组坚持原则,依了洪笑峰的话,早就是奇冤大案了!”他也由于心情太激动,百感交集,公布了这件事后,居然反常地没做任何解释,连平常会议固有的客套话也没说,更没向任何人招呼,就转身独自离开了会场!
赵成和宣布了这个结论的第二个礼拜,人保组整体撤出了韩庄,回县城去了。
从此,王元新不论什么事都要大家找赵荣雨决定。而赵荣雨也只是做些日常工作中矛盾的调解。正式生产仍然以王元新为主。
几十年的大集体生产制度,社员们形成了“太阳满天过,天天有活做”,做多做少,做好做坏无所谓,只要有工分,混一天算一天的态度,习惯地产生了“大家的事,靠我一个人不抵事”的大呼隆思想。这情况是所有生产队的通病;更是使生产拖拉,无法治理的难题,也是部分想搞好生产的人共同的话题。
各个生产队有方法、有机谋的老农有的是。只是由于日常的矛盾,常常弄得坚持公道的人“吃力不讨好”。虽然现在是“三级所有,队为基础、自负盈亏”的体制,生产的好坏,直接影响着社员自己的生活,可是,层出不穷的矛盾日渐尖锐,几乎没有人愿意坚持原则,大家只能拼着一样穷。
赵荣雨在学习大寨经验的启发下,建议东风队尝试着“多劳多得,按劳取酬”的方法。这种方法试行后,初步尝到了“按劳取酬”的好处。粮食总产量比红旗小队高了七千斤,单产超过了历史上的任何一年。
试行“多劳多得,按劳取酬”后,虽然实现了男女同工同酬,促进了生产,可是矛盾却多得层出不穷:定下的一天工分,承包给个人,实际没做到半天就完成了,质量却是一塌糊涂。稻秧插在田里,不是稀得行间里能行船,就是横捺直捂地按在泥土里;割过的稻子,掉得满田都是,看了叫人寒心。林林总总,你有政策,他有对策,只顾自己多记工分,不管生产效果。正因为这样,所有的生产队,宁愿放任拖沓,也不愿意实行“按劳取酬”。
1974年年底改选,东风生产队取消了“政治队长”的职务,赵荣雨被选为生产队长,王元新做了副队长。这一年,赵荣雨决定全力推行“按劳取酬、多劳多得”的生产方法,但是,还要加上“质量第一,纪律第一”的管理方法,力争要把社员们劳动积极性真正调动起来,体验自己在管理上的作为。
赵荣雨被确定为生产队长以后,便与全队人认真地订立了确实可行的生产制度。日常工作中,他身体力行,排除狙牾,认真执行,使这些制度得到了全生产队社员的拥护。这一年生产获得了空前的好成绩:粮食单产超了“纲要○1”,是866斤;总产几乎翻番,比原来东圩队(东圩全村一个队)最高产的1965年只少6000斤。分配虽然受政策限制,平均口粮也分到了750斤。对国家,不仅完成了征、购,卖出的“三超粮”,比征、购的总和还多8000多斤,还存留了两万斤储备粮。普通劳动力做的工分也由每年的250个左右,上升到300个出头,高的竟是360个;妇女、半劳动力的工分数增长之巨,直飙男劳动力。每个工分值破天荒地达到了1.20元, 4.5斤稻谷。人们从共产风一直到了今天,才从真正意义上解除了粮食紧张的恐惧心理。然而,也仅仅只是解除了粮食恐慌而已。
1975年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1976年赵荣雨被吸收进了共产党组织,调到大队当了党支部副书记,这一年他29岁。从此,他基本脱离了与东风队社员朝夕相处的环境。他和社员们制定的生产制度,东风队还在沿用,红旗小队也学了去。可是,因为矛盾层出不穷,常常弄得队干部们黔驴技穷。这两个生产队的生产,虽然在韩庄大队仍然领先,而这些制度,却被日常矛盾弄得百孔千疮。人志各异,矛盾重重;都说这大集体的日子,只能在矛盾中苟且。
1976年9月9日,毛主席逝世。10月,以华国锋为主席的党中央粉碎了“四人帮”。其后,邓小平力挽狂浪,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开展理论大讨论,扭转了长久统治中国 “政治挂帅” 的路线。1977年10月18至22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了“阶级斗争”的政治路线,实行了改革开放的政策,国家的工作重点由路线和阶级斗争,转移到了经济建设中来。从此,中国政治形势从虚妄走向了务实。
被“政治审查”长达八年之久的赵荣春,直到现在才算被解放了出来,调到了谷口人民公社当任了党委书记兼革命委员会主任。他由政治囚禁到精神解放,犹如死而复生。因此,他感慨地说:“当时天天喊文化大革命万岁,幸亏没有‘万岁’得起来,要不然,对我的审查,也将会是一万年之久!”
1979年3月,国家一次性地把“四类份子”都揭掉了帽子,使他们有了与普通社员一样的社会地位。可是,东圩村的两个四类份子都已经死掉了,他们一个也没有来得及享受这样的待遇!
1980年春节,大家都欢浸在不曾有过的祥和热闹的氛围里。赵荣雨虽然担任着大队副书记,可是,他却“每逢佳节倍思亲”。晚上,一个人在书房里,缅怀起他的三弟来。想起了他当时的情景,想到了他的音容形状,伤心得痛哭涕零。他展开了一张纸,泪水竟然把这张纸淋得湿了。他用颤抖着的手,执笔写下了怀念三弟的文章○2来。
哎呀,多愁善感的赵荣雨啊,都二十年了,你还耿耿于怀?
社会虽然正在回归自然,可是,赵恒发身体却越来越糟,几乎不能做农业了。他为了经济有所进益,希望做点力所能及的事。于是,想到了开个小商店。赵荣雨知道,像东圩这样的村庄,开个小店,实在是方便大家的好事。可是,他也知道,开店是要得到工商部门批准的。于是,他特别来到谷口工商所,找到了刘所长。刘所长却不肖理会地说,农业人口根本就不能从事商业!赵恒发知道了这一情况以后,只恨自己命苦,为什么就不能是非农业人口呢?这一年的春节当中,赵荣春来了,赵恒发与他谈到了想开小店不被批准的事。赵荣春回到谷口后,与合作商店的朱经理说了,朱经理同意在东圩村设个临时代销店。这样,赵恒发才算实现了开小店的愿望。
1979年秋天,新镇公社调来了一位姓唐的新书记。第二年的春天,一河之隔的南陵县的农民自发地将集体土地分到了自己家里,搞一家一户的生产。唐书记知道了这个情况后,在各种场合都批判南陵农民的作为是“搞资本主义”。他说,我们新镇决不允许那样干:“如果谁敢分田单干,我就坚决与他斗争;新镇要想分田到户,除非我姓唐的不在这里工作!”
其实,这时候安徽凤阳县的小岗村十八户农民已经立下了“生死状”,强行将集体的土地分到了家里,得到了省委书记万里的许可,社会上的农民都在群起而效仿,出现了“要吃米,找万里”的民谣。然而这个消息却是被“封锁”着的。
人们为了尽快摆脱大集体的牵制,在唐书记的压制下,变着方法,改变生产环境。在“学习大寨”的掩护下,明目张胆地将生产规模缩小,美其名曰加强“责任制”。先是将生产队一分为二,称其为生产小组;接着,又将小组划分。不断地“二一添作五”的分法,到了1980年,生产规模实际上只是三、五户了,而且多是兄弟组、父子组,也都是“独立核算”。由于这样的小组仍然受着“集体”的牵制,因此人们总还盼望着没有牵制、自由自在的生产环境。
到了1981年清明,人们见南陵的“资本主义”并没有纠正,便不顾压制,群起而动,硬是把集体的土地划分到了各家各户。可是,由于不是正规的划分,仅是匆忙而将就的措施,田虽然分了,却留下了一些不应该有的矛盾。
分田到户以后,大队、公社的干部们只做着计划生育和收取各项摊派款的工作,对农业生产则完全不过问了。关于分田,他们更是懵懵懂懂,无可适从。到了第三年,即1984年,为了明确负担,才给各家各户发放了《土地承包负担卡》,把原来生产队的负担,按照田亩数字明确地划分到了各家各户。这样,人们才知道分田到户,叫做“土地承包”。而“承包”的 土地,是随时要收回集体的。因此,许多生产队每年各户人口增减,土地也跟着进出。这给大队和生产队干部,出了许多难题。
东圩人分到了田土后,从忐忑不安到吃了“定心丸”,是到了1995年省政府正式的发放了《农村土地承包合同书》,而且还规定三十年不变的时候。这时候,凡是上了合同书的土地,都不再随着人口进出了。也是到了这时候,人们才如梦方醒,后悔当时分田太没有慎重的后果。可是吃亏的,上算的,耕作上矛盾的,已经成了多年的事实,都只得随之任之了。
分田到户后,农村的自由与和谐的气氛自然形成,人际关系友善起来,人情网络又复活了。生产效率更是迅速提高,粮食产量像玩魔术似的增长。当时一个生产队的产量,只是几户就收了起来;而且劳动力大量空闲。
由于劳动力大量的空闲,农民们又从事着粮食生产以外的多种经营。于是,各式农产品都上来了,社会物资奇迹般的丰富起来。一直匮乏的市场,繁荣得应有尽有,呈现着饱和状态,甚至到了惟恐卖不掉的程度。于是,统治市场几十年的粮票、布票等等票证,自行的失去了作用;无钱无市、有钱也无市的情况,终于变成了历史!
在务实的经济大潮中,城市经济也奇迹般地崛起。广大农民在自由与和谐的形势下,自发地涌向城里,参与城市建设。他们虽然受着人为制度的歧视,即只能以“农民工”的身份,在城里“打工”;然而通过辛勤的劳动,却也丰富了自己的经济收入,改善了拮据的生活环境;同时也填补着城市与农村、农业与非农业的巨大鸿沟。有着机会改变自己命运的农民们,初显身手,便展现了应有的能力。回首刚刚过来的日子,他们都由衷地感叹道:
“几十年来,我们就像是养媳妇一样,天天被公婆教训,还食不果腹,衣不蔽身;又像是被牵制着手脚的木偶,弄得晕头转向,毫无应有的主动权;更像是被困在井里的大牛,虽然有浑身的力气,却没有奋斗的余地!开放了,才算是真的放开了,我们有奔头了!”
1982年,国家撤销了革命委员会,公社和大队两级都被叫做管理委员会;1984年撤销了人民公社,行政上恢复了乡政府,大队叫做行政村,生产队叫做村民小组。政治形势一天一天地趋向稳健与开放,农民们才算有了真正的自由与和谐。这群曾经自己比如是被“困在井里的大牛”们,才算真正的跳出了困境,有着驰骋的广阔空间!
赵恒顺、董正玉和鲁老二,都是曾经的生产队长。在经历了巨大的社会变革后,因为都上了年纪,不能外出打工,经常在一起抚今忆昔。他们老是从“跑长毛反”一直谈到“改革开放”,总是感慨万千,感叹自己有幸趟过了非常岁月。综合他们谈的最多的内容,竟是下面这一小段话,也能算是他们的心声:
社会的太平,是人们所企盼的;然而却不能算是和谐的社会。和谐社会的形成,决定于国家政策。只有和谐的社会,才是人们的福气。农民们安居乐业,也只有在和谐的社会里才能做得到。要是社会能够始终如一地维持和谐,农民们就会很自然地谋求到恬适的生活。事实反复说明,农业是社会的根本;只有农民们真正安居乐业,并且丰衣足食了,整个社会才能真正繁荣昌盛得起来!
①纲要:农业发展《纲要》规定,江南地方亩产800斤。超过这个产量,叫超了纲要。
○2赵荣雨《哭三弟》的文章写于一九八零年二月十六日,农历庚申年正月初一日夜,全文是:
每逢佳节倍思亲,忆及三弟泪淋淋!
三弟乳名叫三牌,一去已经二十载。每每忆及悲欲绝,音容耿耿在胸怀!
年仅六岁身型大,瘦如骷髅骨还宽。只因腹中饥辘辘,终日倚门盼母还。
慈母下田难有空,只有三餐饲儿肠。水糊一勺仅润喉,幼儿终日饿嚷嚷。六岁只会一句话:“毛毛要的(吃)”口头禅。只恨菜糊量太少,不论好歹不端详!纵然从来不择食,从来没曾饱肚肠!
当时人情大检验,夫妻母子不顾恋。只为活命各顾各,惟有我母德殊贤。慈母终日似空腹,还为孩儿省口粮。那时母亲年虽壮,只剩骨头与皮连!二弟腹痛常生病,我也浮肿快死亡。唯我三弟无大碍,只是要吃事一桩。时人议我四口人,必作饿殍难周全!
寒冬已过虽是春,我家父母心犹寒!忍饥挨饿难尽日,为保性命费端详!
父亲矿山弯子店,食堂粮食稍为宽。那天晚上探家来,为救我们细商量。两个弟弟都睡熟,父母议论到天光。惟因事情特重大,触我童心永不忘!
父亲起初不愿意,母亲苦苦陈端详:“三个孩子放一个,困在一起都会完。放走一个多个粮,补贴家里能稍宽。矿山粮食较宽裕,孩子送去都收养。你在那里能照应,要想接回也便当。”母亲话儿决定事,至今仍响我耳旁:“大孩已经能懂事,能说能写送不便;二孩身体不大好,送出难保命安全;小三年小不会说,只要有吃就平安。”于是决定送三弟,留他口粮救我们!
为了能留三弟粮,父母悲声不敢张。悲声一出少了人,口粮马上扣个清;父亲矿上不敢讲,讲了要退三牌回家程。回家虽好却违意,要想逃命又逃不成!
万般后果都想了个遍,就是没想到无回人!
翌日天阴无太阳,天还没亮动了身。父母三弟到新镇,买碗豆渣慰弟心。三弟年幼不知事,只谓充饥有余兴。吃罢父亲背他去,举步向那矿山行!
母亲回家偷着哭,哭声至今恸我心!
父亲叙他弃子情,有谁听了不寒心:到得矿上买麻饼,一个麻饼断儿情!“毛毛在这站一下,阿爸还买饼干给你的(吃)。”此话竟是父子永诀音!三弟听说有的吃,盼食之情兴纷纷。其实此是弃他去,他哪知道其中因!
天茫茫,地暗淡。三弟站在那儿望眼穿!阿爸竟然没有回,他呼爹喊娘无应声!
神可守口人不守,我村食堂消息灵。三弟走后第三日,他的口粮被扣清!
三弟在那弯子店,失却亲人多彷徨:一日父亲去剃头,见了父亲不敢喊——呆呆傻傻失了神!岂是不敢喊哟,不敢喊!陌生之处多凄凉。在家虽饿却受宠,顿然成孤心猝寒!满目生人无怜者,寂寞恐惧已呆板!
十多日后忽不见,父亲到处曾打听。人说板车已带走,带到哪里说不清。又说弃儿多半死。死后弃去无死尸。小麦黄时母心焦,亲去那里寻小儿。小儿没曾寻得到,自己好险把命抛(请见本书第八十三章)。
年下母亲再去找,没见其人只见衣。是死是活说不定,我家三弟孰归期?
时间已去二十载,三弟形影在我心。那时我才上小学,上学之余伴他身。三弟多是我携带,手足之情格外亲。写此心恸泪长流,每每停笔吞哭声!